【史志论坛】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的编纂及其文化意蕴——以贵州旧志为考察中心
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的编纂及其文化意蕴
——以贵州旧志为考察中心
谭德兴
提 要: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散文文体作品众多。不同时期,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作品编纂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嬗变呈现出深刻的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其一,充分体现史学与文学的密切互动。其二,体现史学与政治的密切互动。其三,呈现出浓郁的西南边省地域文化特征。贵州方志艺文志中散文文体编纂的发展,是史学、文学与政治在边省区域文化中的有机融合,显示边疆史学发展的特点与成就。
关键词:方志 艺文志 史学 文学 边疆治理
方志艺文志主要有两种编纂体例,一是目录解题式叙录艺文著述,二是文选式全文收录艺文作品。方志艺文志是按文体分类来全文收录作品,从大的文体分类看,不外乎诗歌、散文两类。诗、文两大类中又可细分为很多文体小类。本文主要探讨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作品的编纂及其所蕴含的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从明至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全文收录的散文文体类型主要有敕、谕、诏、奏疏、露布、状、颂、书、赞、箴、语、铭、论、解、教、难、考、辨、说、书后、墓志铭、问答、经义、传、志略、序、纪、记、引、跋、檄、文、议、公移、示、杂记等。不同时期的方志艺文志,收录散文文体作品的次序、类型和数量各不一样。我们选取几类比较典型的散文文体作考察,以具体探究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编纂所蕴含的史学、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揭示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的思想内涵和特点,有助于中国方志学及边疆史学研究的新拓展。
一、敕谕类文体之编纂:政治管辖的宣示与教化
敕、谕等文体,主要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对下属的命令与告诫。这些文体在明代贵州方志艺文志中却没有被收录。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均未收录勅、谕等文体作品。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首列的是诗类作品,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首列的是记类作品。明代贵州省志艺文志编纂虽然没有收录帝王的敕谕类文章,但府志中却不乏此例。如嘉靖《思南府志》,其书虽然没有设置艺文志,但却在卷8专收诰敕,且说明“诰敕者,王言之敷,而邦家斐如者也”“且见天子龙光,无远弗被也”。显然,嘉靖《思南府志》单列诰敕成卷,彰显的是封建大一统政教思想。

贵州省志最早开始收录敕、谕等作品的是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紧承其例。康熙《贵州通志》卷31《艺文志》首列的是敕谕文,最早一篇是宋太祖谕敕,即《谕普贵敕》:
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征伐之兵,征讨之典。予往年为扶播南杨氏之弱,劳我王师,罪人斯得,想亦闻之。有司因请进兵尔土,惩问不贡。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穷兵黩武,予所不忍。寻乃班师。近得尔父子状,知欲向化,乃布兹文告之。尔若挈土来庭,爵土人民,世守如旧。予不食言,故兹制旨,想宜知悉。
此谕敕最早见载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3“贵州宣慰司下·人物”条目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没有艺文志,故该志虽载录宋太祖谕敕,但仅仅只是作为征引资料来印证历史人物,这种载录既没有方志编纂的文体意识,也没有首列敕谕的政教目的。而至清康熙时期,中央政权基本完成对贵州的改土归流,真正实现对西南地区的大一统,故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首列敕谕,实质宣示的是对边徼地区的政治管辖权。这也是清代作为边省贵州,其史学发展的政教内涵与重要特点。故乾隆《云南通志》卷29《艺文》:“我国家重熙累洽,圣祖仁皇帝削平僭逆,文教诞敷,世宗宪皇帝垂念万里,边方训谕谆挚。今皇上即位,洪慈厚泽,无远勿届,谟诰所颁,煌煌乎俪日星而昭云汉,丕显丕承,于斯为盛,宜恭冠艺文,以为裔土之光。”“无远勿届”“裔土之光”,这充分说明,方志艺文志首列敕谕类作品,宣扬的正是封建大一统政教思想。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无疑遵循的正是这一原则。
宋太祖《谕普贵敕》,为最早提及“贵州”的,其主要内容为戒谕“远在要荒”的贵州彝族首领普贵,“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征伐之兵,征讨之典”,宣示的是中原王朝对僻壤贵州的控制,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意味。宋代的贵州虽然属羁縻之地,但北方赵氏政权并没有将其排斥在自己的版图之外。现今贵州锦屏县诸葛洞内石壁上还保存有一诗刻和一篇《诫谕文》,作者分别是南宋将帅张汉英、郡守张开国,书写时间为景定辛酉(1261)戊戌月,景定为南宋理宗年号,锦屏诸葛洞内石壁上的诗文,记录南宋军队在公元1261年对贵州锦屏当地苗、侗等少数民族的征讨,宣示对贵州“蛮族”进行征讨的战功,警示当地少数民族不得反叛朝廷。此充分印证宋太祖《谕普贵敕》的戒谕。
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紧接着又大量载录明太祖、明孝宗等敕谕,如明孝宗《谕都匀府敕》:
朕惟都匀远在贵州东南,因无流官抚治,往往自相杀夺,不得安生,而又时出劫掠,为地方之害。近因贵州镇巡等官奏请,特敕大师征之,既已克平。各官奏如永乐年间事例,开设府治州县,铨除流官抚治之,以警其后。今从其请,设立都匀一府,而以新开独山、麻哈二州,清平一县,并旧设都匀、邦水、平州、平浪四长官司,属其管辖……使之日染月化,而皆囿于华夏礼法之中。
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录的明代谕敕,或命对西南洞蛮之征剿,或令对乌撒乌蒙、水西等地之教化与讨平,或论在都匀置流官设府州治理。其记载内容多为中央政权的治边方略,充分显示明代贵州与中原政治文化之碰撞、交融,宣示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省特别是贵州开始的实际政治管辖。
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还收录大量康熙间敕谕,内容多为对贵州之免输钱粮,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谕免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钱粮》:
谕户部:黔省为滇南孔道,地瘠民贫,大兵凯旋,挽输刍糗,供应人夫,极其浩繁。且起解吴逆,家口络绎运送,不无苦累,恐小民竭力供亿,生计艰难,朕心深为悯恻。所有本年秋冬及来年春夏应征地丁正项钱粮,尽行蠲免,以示朕勤恤民隐至意。
康熙间,清廷之所以免输贵州钱粮,一是因为贵州本来土地贫瘠,收入不丰;二是清初平定吴三桂之乱,实际上贵州成为主战场,战争对贵州百姓带来巨大损害,民生凋敝,需要休养生息,故清廷不得不免输贵州钱粮。
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也有载录御制碑文,如《御制云贵总督殉难加赠兵部尚书谥忠果甘文焜碑文》。这是对殉难云贵总督甘文焜之褒奖。又康熙二十二年《谕祭三等伯提督赠太子少保谥忠毅王之鼎文》,康熙三十年(1691)《御制三等伯提督赠太子少保谥忠毅王之鼎碑文》等,此为御制太子少保王之鼎碑文,均为旌表大臣忠义之节,引导教化,显示以风化下的移风易俗作用。
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对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所列敕谕文全部收录,又新增一些敕谕文,如《雍正六年抚绥生苗》等,多是对贵州苗民的抚绥与教化,显示清代初年至中叶,清廷对贵州政治控制的强化与教化的渐见成效。
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的散文编纂大多沿袭康熙、乾隆《贵州通志》首列敕谕文的体例。如道光《大定府志》、《贵阳府志》即谨遵此例。光绪《黎平府志·艺文志》即便没有按文体收录作品,但在开列著述目录前亦大量全文载录皇帝上谕。这些散文编纂自然是封建统治忠君思想充分体现,同时也反映清代封建统治对文化思想领域之严格管控。此编纂思路至民国时期发生转变。如民国《续遵义府志·艺文志》卷33收录全文作品时虽然首列的是敕制文,但数量明显减少,只有3篇,分别为袁桷代拟的《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治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上护军杨汉英赠推忠效顺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封播国公谥忠宣》和《杨播国公妻田氏遵义郡夫人加播国夫人》,王构代拟《播州杨邦宪赠谥制》,此3篇敕制文全为元代文人代拟,主要涉及与播州相关的历史人物杨汉英夫妇、杨邦宪的赠谥。这与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首列大量皇帝敕谕的做法明显不同,不但淡化了封建帝王因素,也表明随社会政治发展,皇帝的敕谕文至民国时期已经没有应用场所,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故除民国《续遵义府志》外,其他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的散文编纂亦不再将敕谕类作为重要文体而进行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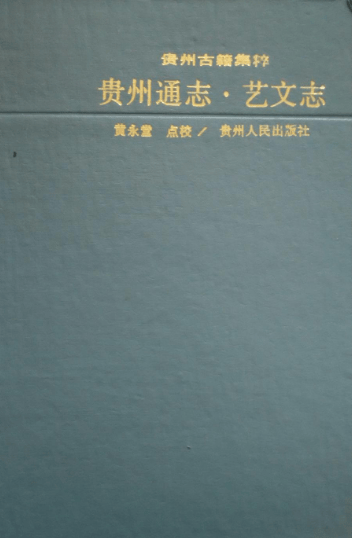
二、奏疏类文体之编纂:边省治理的思考与举措
奏疏,是大臣对皇帝的进言,属官吏对上之建言献策。明代贵州方志艺文志对奏疏是不重视的,不但将这种文体排列在后,而且收录数量极其有限。嘉靖、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都只收录提学谢东山《建盘江河桥疏》一篇:
头兰故地,尾洒新亭。水绕盘江万里,东驰海峤湍流。束峡两涯,下俯冯夷。孤航才受两三人,旅客每劳昏晓候。黄茅瘴起,魂销贵竹之程;僰道烟横,望断长安之日。欲教坎窞为平地,须易舟楫以桥梁。何官府执匮乏以为辞,而小人乘险危以为利。悠悠作道旁之议,凛凛为徼外之虞。今遇巡抚刘公,轸念时艰,力行王政。远惟蒲津系缆,开元尚倚于铁牛;近羡澜沧引绳,壮观犹多于金马。爰引刍荛之一得,更添人鬼之佥谋。巨石中流,名称虎跳;崇基近岸,势便鸠工。用倾府藏之资,经始恢宏之制。仍赖多方助役,剩期一举成功。人人任占八福田,荡荡平铺五尺道。彩虹嶻嵲,无分春夏秋冬;乌鹊参差,那限东南西北。看取杜元凯举觞之乐,何如郑子产乘舆之恩。
此名为疏,实为纪功颂德。赞美巡抚刘公修建盘江河桥的功绩。全文采用四六骈体形式,首先渲染盘江之地势险恶雄峻以及交通不便,次叙巡抚刘公体恤时艰,倾心力行集资修建河桥,最后讴歌建桥的功效与美德。收录骈体文疏奏,这在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算比较有特色的。可能这也是明代贵州方志编纂者的文学观念的体现,因为其将那些没有骈体特征的奏疏几乎都放在《经略志》中收录。显然,史志编纂者的文学观念,对方志艺文志的文体收录产生较大的影响。
到了清代,对奏疏类文体的文学性要求明显降低,而注重的是这类文体的政治属性。康熙《陕西通志》凡例云:“艺文……奏议关系最重,非有宣公之心,不能为宣公之言,今于前代奏疏后,即缀本朝本省奏议,谓其心有一揆,许以先后接踵尔。”这里明确强调方志艺文志编纂对奏议的重视。故清代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疏奏地位明显提升,其排列顺序仅次于皇帝敕、谕、诏之后,且数量明显增多,内容也十分丰富。例如,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明代疏奏13篇,分别是王宪《请忠烈庙南公祀典疏略》,王琼(乾隆《志》作邹文盛)《叙捷疏》,杜拯《议以楚卫增贵州疏》,田秋《请开贵州乡科疏》《补遣策疏》,邹元标《吏治民瘼疏》,林乔相《请广额疏》,郭子章《开平越新疆疏》《题设府州县疏略》《题设新贵黄平等学疏》,李时华《题增设县学疏》,萧重望《题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冯晋卿《题表吴氏节烈疏》。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奏疏,都是关于贵州政治、文化建设的建议与措施,具体可分为行政区划设置与建设、忠义节烈倡导与旌表、教育发展改革与措施等。其中很多奏疏,对贵州文化发展至关重要。例如,田秋《请开贵州乡科疏》:
臣秋,原籍贯贵州思南府人。窃惟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然后进于大廷,命以官职,真得成周乡举里选之遗意,所以人才辈出,视古最盛。惟贵州一省,边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上维新之化又八年于兹,远方人才,正如在山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谓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也。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镇远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 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旧额二省共取五十五名,云南三十四名,贵州二十一名。臣请于开科之后,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则远方幸甚。
作为一名曾经赴云南参加科举考试的贵州人,田秋深知本省没有独立开科乡试的艰辛。其以自己亲身经历,结合贵州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云贵之间艰难险途,陈述贵州独立开科乡试的好处,与之前未独立开科的种种弊端。田秋上此奏疏时间是嘉靖八年(1529),之前贵州乡试一直挂靠在湖广、云南,贵州人得远赴外省参加乡试,路途遥远,行程艰险,花费巨大,严重阻碍贵州人才选拔,自然也滞后贵州文化之发展。经过田秋等一批人不懈争取,明朝终于在嘉靖十六年“从巡按王杏请定贵州本省开科乡试”。康熙、乾隆《贵州通志·选举志》载有明代贵州进士名录,以嘉靖十七年戊戌为界,之前明代169年中就试湖广、云南中进士者只有29人,而独立开科乡试后的106年中,贵州中进士者73(乾隆《贵州通志·选举志》比康熙《志》多崇祯庚辰科1人)。明代贵州开科乡试后中进士数是之前就试湖广、云南时的2.5倍。这充分说明田秋《请开贵州乡科疏》的重要意义。
与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较,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在收录明代奏疏时有所增减,如田秋,继续收录其《请开贵州乡科疏》,新增《请预筹流民疏》,删除《补遣策疏》。新增李化龙的《平播疏》《播地善后事宜疏》,充分说明清代以来对边疆治理意识的加强。收录前代治边奏疏,无疑是给当代提供借鉴。特别是李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涉及贵州部分区域经历巨大战事后的恢复事宜,包括12事:复郡县、设屯卫、设兵备、设将领、丈田粮、限田制、设学校、复驿站、建城垣、顺夷情、正疆域等。这些是明代经过平定杨应龙反叛之后得出的治边经验,也是清代值得借鉴的边疆治理方略。清代自康熙始,对边疆治理十分重视,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逐渐推行之深水处,清廷与边省少数民族的矛盾凸显,康熙、乾隆、嘉庆都有对贵州用兵,如何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明代李化龙的奏疏无疑可提供重要借鉴。清代贵州方志收录清人奏疏数量亦不少,其主要内容与收录明代的奏疏相似,核心都是围绕着边省治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治理而选择。例如张广泗《议覆苗疆善后事宜疏》《苗疆告竣撤兵疏》,其主题以及一些措施实质与李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一致,都是平乱后的边疆治理方略。收录奏疏,在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继续得到体现。如民国《续遵义府志·艺文志》、民国《余庆县志·艺文志》等均有收录奏疏类文体。民国《余庆县志·艺文志》说:“奏疏议论,未尝不炳炳烺烺,一挥万言,皆经世之文,历千载而不磨灭也。”此说明民国贵州方志艺文志之所以收录奏疏类文体,正在于其“经世”的政治色彩。
三、记类文体之编纂:社会发展的实录与成效
记类文体作品,在贵州方志艺文志中收录是比较多的,而且分类与思考也是最成熟的文体之一。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记类作品38篇,按行政区划来收录,稍显凌乱。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中的记类作品放在《艺文志》之首,且分为记上、记下两部分,共98篇,每部分又细分多类。记上部分有题名类18篇、黉序类23篇、祠院类7篇;记下部分有建修类17篇、亭馆类13篇、胜概类10篇、纪功类4篇、杂记类6篇。这些分类主要是根据记类作品的具体内容来划分的,分类细致,收的数量较多,有些篇幅很长。如此细致的分类,大量收录,足见贵州方志编纂者对记类文献的高度重视。这种编纂思想,有其时代特征。例如,嘉靖《常德府志·艺文志》收录诗文次序与数量为:记21篇、序7篇、祭文1篇、书2篇、言1篇、辩议2篇、赋咏。其先列散文,后列诗赋,首列记类,且数量绝对高于其他散文文体。这种诗文编纂是有明确思想做指导的,故嘉靖《常德府志》卷18《艺文志》云:“文以载道。艺文之首《纪述》,固理道之攸寓而政治之得失系焉,非但存建立岁月与作者之名氏焉耳。”这里,揭示首列“记”类文体的原因,那就是记类文体寓含理道,且关系政治得失。这种编纂原则发挥的是文以载道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散文文体时,记类数量最多,而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不但首列记类文体,且收录数量近百篇,遥遥领先其他散文文体。
明代贵州方志艺文志所收录的这些记类作品,蕴含丰富的贵州历史地理、教育文化等珍贵资料,是考察贵州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例如,范汇《八番顺元宣慰题名记》: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牂牁之表,殆古鬼方之境欤。蛮獠种落杂处,叛服不常。入我国土军徇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使都元帅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领万户府一,镇抚司一,安抚司十,长官司五。而顺元、思、播三宣抚地,皆听抚镇,其任可谓重矣。然而四外督土官相袭,或有争则境内寇夺乘衅,道路欲塞。又外连南诏、岭徼、两江、溪峒,侵削斗阅,往往有之。阃政相驰,即戒不虞,故官于阃府者,号称才难。至正十年秋,宣慰司都元帅完泽公以省台宿望,仁勇兼著,莅政未数月,号令肃然,旌旗为之出色。于是纪纲立,法度行,百废兴。而大府未有题名之石,实亦缺典,何以昭劝惩,乃命立石。属余次序而题著之,将镌刻以候来者于无穷。及考诸闻见,始自开辟以迄于今,至于边政之得失,才谞之崇卑,则人心公论,在将历指而议之,可不惧哉!此题名记,述说八番顺元宣慰司的演变历史,以及其下辖行政区划情况。还涉及八番顺元宣慰司的风土人情,以及宣慰司都元帅完泽公治理政绩。题名勒石,实际起到昭劝惩的警示作用,告诫历代郡守,以边政为己任,因为政治得失必定会有后人评议的。又知府李濮《贵阳府题名记》:
贵藩省会,故无郡治,隆庆三年己巳,徙附郡程番而更置之,其事则宪伯纬川冯公记之详矣。初,贵之列郡,官不必备,因其简也。兹郡附省,事务稍剧,则官联具列焉,意重首郡耳。是年孟冬,予承乏首莅其事,寮采以次,而至又逾三祀,制度渐备,骎骎然与内地相埒矣。佥谓立石题名,制不可缺,知其颠末者莫予,若当自系数语,以弁诸首,予则何言哉?尝闻今之郡牧,古刺史职也。宣德达情,缉绥纠正,百责萃焉。矧附居省治,诸当道日,临之贤易,知否易訾。且又创置方新,纪法未具,处军夷之杂扰,无州县之联属。居是任者,其艰理之势,较他郡岂不倍哉!思其艰,图其易,谨厥始,虑厥终。予固不敢自诿,亦不能不为同事及将来者望也。于此而不有以纪之,则稽核无资,监观无措矣。于政治何裨乎?夫知官秩之不可以无纪,则当思纪之不可以为易,使其纯然而可为后人之观法也。则于斯石为有光矣。则凡所以守身与物之间,用人行法之际,固哲人之所择也,充是心也,则自今以往,当必有瑰玮卓荦之才,以开大其治懋建俟树屏之绩,成深远能迩之功,易夷俗而媲中州,重光叠盛有,非记之所能尽者矣。今日之记岂徒秩官爵叙名氏著乡土,以为一时之荣观尔乎!同寅诸君以予言为然,遂命工刻之。
此题名记与前引范汇文章一样,不是以著录官爵名氏为重,而是以阐述贵阳府郡治之责任为核心,反覆论述强调,娓娓叮嘱,所有的目的在于希冀历任知府以建树易俗为己任,尽职尽责,时时以刻石督促自己。
黉序类则主要是记载学校教育情况,纪事色彩浓郁。例如,江东之《贵阳府新建儒学记》:
明兴二百年来,声教丕隆,蒸沦翔洽,讵惟函华鞶帨,即穷蕃荒服,亦胥渐被。盖家弦户诵,其磅礴匪朝夕矣。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辟干肇造后,遂得列为藩服。虽治杂汉夷,乃百司庶政概视两都诸省有差无异,而贵阳尤黔省首郡,故牂牁程番地,更始于穆考御极之三年,明年秋始设学,如令甲一时规橛未备,姑就阳明书院改署明伦堂,群博士弟子员讲业其中,若圣庙贤庑,所为瞻礼陈乐也者,则第因宣慰而贵阳附焉。夫使邑学隶府,犹曰俭制,岂其改郡改名而于弘风训典之要地,顾让而未遑耶。大都崇儒表正,在朝廷作兴倡率,在有司而尽制备物,又自有时为之耳。万历甲午春,当事者始兴创建议,遂于会城门北得吉壤焉。昔为蜀行都司,今割入黔,偃武修文,实相迭运,固山川灵秀所钟,最胜之遗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于是鸠工御石,经始告成,亦阅三年于兹,会余被命抚黔,下车首谒宣师,瞥见庙貌鼎新,丹楹刻桷,云构翼屹,怪而问之,乃知昔也有待。今始考焉,时乎渐次,莫或亟之。余徘徊凝睇,自公宫以至堂奥,若两庑祠斋,圜桥亭阁,悉中程度,且也地不烦改辟,用不伤公帑,民不废时务,制不逾泰靡。问谁赞助则分藩郡邑,问谁经理则更老荐绅而黉序之。能事毕矣。……遂谋之刘守,而勒之于石。
此叙明代贵阳府新建儒学始末,反覆论述,核心在于弘扬儒教,通过不断创建官学教育体系,来传播儒学,希望能有一天,使贵筑变成邹鲁。于此也可知,明代儒学在贵州传播的具体表现。这也是贵州文化能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因。
记类中的修建类,主要是对府署、城池、桥梁等修建的记叙,如刘秉仁《都匀府重修郡城记》、陈尚象《麻哈州新建惠民桥记》、陈南星《重修思南府署记》等。此类作品在纪事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歌颂政德色彩。亭馆类作品,主要描绘一些人工建造的亭台楼阁等著名场所,如王守仁《君子亭记》《玩易窝记》《月潭寺公馆记》等,颇具浓郁人文内涵。胜概类作品,主要描绘一些著名自然景观,如焦希程《云龙洞记》、田汝成《清平天然洞记》、祁顺《镇远游西峡记》等,有一定纪游色彩。纪功类作品,主要是歌颂封建统治所谓的“平蛮”“平苗”“平夷”的战功,这实际上是封建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的镇压与征讨,是以武力为手段的一种政治文化输入。杂记类作品主题不统一,涉及社会生活多方面,如李学一《马政所碑记》谈的是马政事宜,田秋《少参蔡公潮生祠记》实为人物传记,王世贞《胡佥宪二义仆记》宣扬的是封建时期仆人对主人的忠义。
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记类作品较多,有3卷,但其又作进一步区分,卷40为记,卷41、42为碑记。将碑记独立出来,这是清代金石学不断发展的产物。划分记与碑记,这是文章载体方面的区别,既体现方志编纂者文体观念的发展,也说明至清代贵州石刻文献的繁荣。而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卷40的记类作品,内容上没有超越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也没有前者的进一步归纳与细分。有很多篇章也是对前者的重复收录,故也不再赘述。其他清代的贵州方志,对记类作品的收录,应该说在《艺文志》各文体中一直是比较多的。例如,嘉庆《黄平州志·艺文志》共3卷,其中第9卷除第1篇外,其余全部是记类作品,占整个收录作品的三分之一。道光《贵阳府志·文征志》收录记类作品有5卷之多,仅次于诗类作品。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记类作品分上下卷,仅次于诗歌作品。整体看,清代中叶以后,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记类作品从细目分类和主要内容上看,基本上没有超越万历和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录的记类作品,而且记类之下细目的划分看,后来的方志也没有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那样详细。但后来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记类作品,也有跳出万历《贵州通志》思路的,例如,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收录黄元治《平远风土记》,宋起《威宁风土记》,田雯《苗俗记》,这些记类作品均没有在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的记类文体细目中。风土记是清代兴起的一种新兴文体,于此亦可见贵州方志艺文志作品收录,是随着文体发展变化而有所调整。另,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收有廖大简的《贞女记》:
贞女者,毕节县黄绳谋女,邱文熊妻也。少娴《内则》,通《孝经》章句,读《列女传》,能属文。及笄,婚有日矣。文熊随宦河南宝丰县,以疾卒。女闻讣,泣血久之。文熊柩归,女泣告逾父,请于舅姑,自为文以奠,斩衰而哭之,辞甚哀。其文曰:“呜呼!惟君髫龄,实为我仪。未经定情,旋即辞世。命之维艰,至于斯极。妾以弱质,少依父母,行年十七,礼聘于君。命遭迍邅,昊天不吊。君适豫省,因病殂谢。伤哉闻讣,念兹伶仃。维日饮血,晨夕摧心。依身慈母,荏苒五载。今母又逝,此身何依?触景涕零,何所控诉。呜呼!夫子,君以成童,妾以少女,未侍巾帨,旋见夭折。生不见面,死不见棺。顾影茕茕,情何以堪!君之灵车,今返乡土。心有所系,身有所属。于是涕泣于父母膝前,吁恳于翁姑堂下,乃命衰绖,匍匐灵帷。呜呼!夫子,于今已矣。瞻帏寂静,呼号无应。惟是父母之命,始之终之。继自今,惟以未亡人之身,谨代子职,事奉翁姑 以终罔极。君如有灵,其知也耶?”女自誓不嫁,归邱氏,奉舅姑,修妇职惟谨。
廖大简论曰:或云,《礼》,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母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又《周官》,媒氏掌万民之判,禁嫁殇者。未闻夫死而终不嫁者。岂古人不之重欤?曰:非也。圣人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期通乎人之情而已。不苦人以所难,未昏而不嫁,人之所难也。倘能矢其志而遂其愿,又何非君子之所取耶?是在《恒》之《大过》曰:“恒其德,贞,妇人吉。”圣人取其从一而终也。如卫之共姜,《柏舟》自矢,曰:“之死靡他,之死靡慝。”贞女其早有感于此,而必能安其志而恒其德也。谨记其事,以告诸采风者。
这是一篇碑记,实际上也是一篇妇女传记,若换成题目《贞女传》,是根本没有区别的。如,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19《艺文志》收录陈熙晋《包贞女传》:
贞女包氏者,四川合江人包大玉女也。女性朴谨,不苟言笑。生数岁而大玉殁,育于其母夏氏,字同邑杨春英。未几,春英随其父迁贵州之仁怀厅。女年及笄,而春英凶问至。仁怀故与合江接壤,女闻哀痛不已,欲奔春英丧,其母与兄难之,数谕以道远难赴而止。女誓不他字。母兄不能强及。母殁,女哀毁逾礼,矢志益坚。依兄嫂纺绩度日,年七十一卒。
论曰:《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以如之。夫未婚而夫死,在女子不可谓未成,夫吊服则斩衰也。既葬而除者,圣人酌求其天理人情之不得已而言。论其至则妇人不贰斩也,今贞女于杨氏子之死,未尝奔丧,且终其身未尝至夫家。疑《礼》经所未有。呜呼!泰伯、伯夷、叔齐,何尝一日立于商之廷,而孔子亟称述之者,何哉?亦论其志而已矣。仁怀至合江城百里而近,余至仁怀访贞女之夫家,无能道其姓氏者。幸《合江志》载其事,遂为之传。夫贞女一孱弱女子耳,不以生死易其志,殆将与采药之逋臣,采薇之大老同不朽,岂不难哉!岂不伟哉!
此贞女传的内容和叙述模式与廖大简《贞女记》毫无二致。都是对妇女贞节之高度赞美,并从个案现象升华至封建礼制高度,其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十分明确。有些散文文体分类虽不同,但实质内容与结构模式则完全一致。
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中,还有罗英《乡征记》颇有特色,记叙康熙初,吴三桂叛乱,其听说长子湘琳被逃兵所杀害,于是还乡寻找湘琳尸首。《乡征记》就是记录他这一段还乡历程,其“闻长子湘琳为逃兵所害,英因还乡求湘琳,乃作《还乡记》,备述乱离事,其言切中时弊,后大吏采其言陈于朝,卒罢卫置县”。这种记类文体,相当于纪事,又杂有日记色彩,在之前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记类文体作品中根本没有。而且,正是因为罗英的这篇记类作品,直接导致清廷撤掉毕节卫,改作毕节县。于是亦可见文学作品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
四、传类文体之编纂:人物品行的楷模与褒扬
方志艺文志所收录的传类文体作品,实质上与方志人物传中的文章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的传类作品,其性质实际上是属于人物传记。方志的人物传记,主要是记叙一方之重要人物的生平与事迹,起到褒扬忠烈,推崇名节,移风易俗之教化作用。这种编纂思路,自明至民国,都一直在贵州方志中得到较好传承。贵州方志艺文志中的传类作品主要分为3类,一是著名官吏与乡贤,二是忠义之士,三是节妇烈女。例如,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载明扶纲《少保忠介邹公元标纪略》:
公讳元标,号南皋,江西吉水人。登万历丁丑进士。观政吏部。一日早朝,见廷杖者,问故,有人答曰:此书生妄议江陵相夺情事,杖之固宜。公啧啧称羡,退而自计曰:吾幸读书,知重纲常,有以律己。又幸而第,当以匡维国事为任。吾得与诸言者同杖,足矣!密自草疏上之,大忤,有旨廷杖,既杖,江陵犹憾,未置论,戍都匀。道由九江,计抵吉水,甚近,公过弗问,明时谪官得持故官体统,即有编籍军伍,惟其名而已。彼处官司,不得绳之以法。公笑曰:此非所以尊朝廷也。奉法无稍逾。初,就张忠简公读书堂居焉,谓问月楼可当天禄阁,备加修葺,廓而大之,为鹤楼书院。进匀庠诸生,讲习其中。文衡徐公为更建云龙书院,扁其堂曰:天地正气堂。表其坊曰:理学名儒坊。公当蒙难窜徙时,徐公独能阐扬隐,亦足传矣。徐公,讳秉正,谓公深明程朱,正派宜为学士,大夫宗于是,匀士翕然归之,号云龙社。陈公尚象时为诸生,独能得公要领,居六年引掖后学如一日,家数千里,母老,恒异一见,公乃移家来匀,若将终焉。常与尚象辈言朝廷事,辄慷慨悲歌,义形于色。至处日用之间,惟种蔬自给,无戚戚容,远近士流负笈趋风,会有召起,授吏给改小天官丞,晋同卿,擢侍郎,终左都御史,卒赠少保,谥忠介公,文章事业可纪者众,兹仅摘其戍匀所有事以备明史之不及,盖终始公之辞云。
邹元标,明代理学名家,因贬谪至贵州都匀。这里叙述邹元标贬谪之原因以及到达僻壤都匀后的所作所为。其一,效法张翀,建鹤楼书院,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其二,组织云龙社,奖掖后生,培养了如陈尚象等才俊。其三,立志在黔南建构理学名堂,不为贬谪而呈戚戚之容。此传主要叙述邹元标与都匀相关事宜,于此可知,理学是如何传播之西南僻壤。同时,深刻认知贵州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一大批游宦贵州的客籍文人,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通过改变贵州教育条件,提升当地文化水平,为贵州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直接推动了贵州文化之快速发展。
又郭子章《黔记》、康熙和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均载郭子章《参政李公渭传》:
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而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及下楼与朋友笑谈,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何如?”嘉靖甲午举于乡,萧然布素,计偕以一仆自随。读《孟子·伊尹耕莘章》,则曰:“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癸卯,蒋公信视学贵州,公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蒋公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蒋公曰:“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公愧甚,以为学十四五年,只成得一个硁硁小人,不觉面赤背汗淋淋也。由华阳知县、和州知州擢高州府同知,至则谒湛甘泉先生于嵎峒中,尝宿廉州公署,梦三蛇绕身,亟挥杖,蛇乃走。诘朝,合浦吏以美珠进,化州吴川吏以兼金进,公皆叱之。笑曰:“三蛇梦破矣,金珠非宝,固吾人蛇蜗哉!”擢应天治中、南户部员外郎,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萑符之警未殄,公集诸僚谕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盗张本。倘多欲则身为溪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盗?弭山中之盗易,弭心中之盗难,敢忘自责!”闻者悚息。入觐,过麻城,从楚侗先生登天台。楚侗示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弘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阙一不可。”对曰:“渭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锲“必为圣人”四字印而布之海内。尝曰:“孔子‘无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着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毋意’脉路,即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毋意’。知毋纤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擢滇左参政。近溪罗公为屯田使,公至与之合并精神,学益进,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浃,从出这身汗。自是欲罢不能。”所著有《先行》诸集藏于家,《大儒治规》行于世。
李渭,是走出贵州的理学名家。此传,详细记叙李渭如何成长为一代名家。事例生动详细,通篇采用记录李渭言行的方式,真实感人,颇具说服力。据此不难发现,勤奋学习与严于修身,是成为思想家的基础,而在真正政治生活中,只有深入思考,严于律己,不断将自己提升至一个更高境界,方才能成为大家通人。这里,用事实揭示了贵州一代名家的成长经历。
又如,康熙《贵州通志·艺文志》载吴中蕃《守棺孝子传》:
贵阳人,不知姓名,天启壬戌,安叛围省,城外居民争入城以避。孝子居郭外独守其母棺不去,贼至城下,义之,不加害,后饿死于柩侧。
论曰:人生难忘者,父母也。父母之爱其子,甚于自爱其身。使其子而遇水火盗贼焉,不惜以其身救之。至于子,则不必尽然。非其忍于亲也,以其身为父母之所爱,一旦捐而殉之,是与于不孝也。此曲体亲心之说胜也。若夫守棺之孝子,其心则异是。孝子曰:“吾亲之棺在,是即吾亲在是。今贼锋已近,吾亲之魄得无恐乎?吾舍之而去,是舍吾亲也。吾不忍舍吾亲,则终守之,柩存与存,柩亡与亡,如是而已,安知其他。”乃贼义之而不害,贼亦自有其亲耳。然何以不周之而听其毙,此其所以为贼也。蔡顺,母终未葬,里中火发,逼顺舍,顺抱棺哀哭,火遂越烧他舍。贼曾火之不若乎?意孝子必有不义贼之食,而弗食,故贼亦听其死,而不之救也。彼入城以避者,卒不免于饿死,而孝子亦饿死,其饿死则同,而所以饿死者则大异矣。使孝子而臣,必能为负幼帝之陆秀夫;使孝子而友,必能为甘冻死之羊角哀矣,吾不知孝子之姓名也,但表其为守棺之孝子,以为凡为子之劝。
此传的论述对象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且真正的传文也很简短。讲的是一个孝子在动乱中守在母亲的棺柩旁不离不弃,直到饿死。事情并不复杂,但此事经过吴中蕃的一番评论与分析,该事件立马被上升高度,臻至舍身成仁的境界。作者设身处地分析守棺孝子的心理,认为导致孝子不忍舍去的根本原因在于子女对父母的孝义。最后吴中蕃感叹,当时动乱中城内城外饿死者不少,但之所以饿死的原因却大有区别。作者高度赞扬守棺孝子的道德节操,如此推崇,并被收入方志《艺文志》,其移风易俗的风化目的十分明确。类似的,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的余忠《胡知府死节传》,敖宗庆《长官官李盤死节传》是从忠烈方面赞扬臣属的忠心。此外,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妇女传记较多,主要记叙妇女贞节,如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载胡松的《李节妇传》,余忠《王烈女传》,李承露的《薛母贞节传》、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载钱邦芑《三节妇传》,陈龙岩《王节妇刘氏传》,卫既齐《梅节妇李氏传》,张大受《节妇余氏传》,福庆《杨节妇孙氏传》等。
传类文体,在贵州方志艺文志的收录,乾隆《贵州通志》达到高峰。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一共收录传类文体作品23篇,是所有贵州方志中收录传类最多的。这可能与当时朝廷的修志思想有关系。雍正六年(1728)《上谕》:“《一统志》总裁大学士蒋廷锡等奏言: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必得详查确核,采其行义事迹卓然可传者,方足以励俗维风,信今传后。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得旨: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可见,雍、乾时期,中央政权对方志编纂中采录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事迹的高度重视,而这些在方志传类文体中得到最好体现,其目的自然在于“励俗维风”的政教指归。其后,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传类作品,逐渐减少,如嘉庆《黄平州志·艺文志》收录7篇,嘉庆《正安州志·艺文志》、咸丰《正安新志》均未收传类文体作品。道光《贵阳府志·文征志》收录作品十分丰富,但传类却只有3篇。而以收录作品数量著称的道光《遵义府志府志·艺文志》根本就没有收录传类文体作品。民国《续遵义府志·艺文志》收录传类文体作品4篇。道光《大定府志·文征志》收传类作品1篇。这可能是因为方志编纂在人物传中已经大量载录一方历史人物资料,例如,道光《大定府志》设置《惠人志》《俊民志》共17卷专录大定府人物,其中又分细目《职官传》《耆旧传》《忠节传》《循吏传》《孝义传》《列女传》等,清廷所要求方志编纂弘扬名宦、乡贤、孝子、节妇的全在其中。为避免重复,故方志艺文志中不再将传类文体作重点收录。同时也说明作为一种独立传播的文体,晚清以来,传类在贵州方志艺文志中呈逐渐退出态势。
五、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编纂的嬗变及其政教内涵
明代,中央政权十分重视方志编纂,先后两次由朝廷颁布方志编纂凡例,即《明永乐十年颁降凡例》《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中央政权对方志编纂的介入,使得明代的方志编纂体例逐步统一。永乐间两次颁降方志编纂凡例,其中均涉及对诗文的收录要求。《明永乐十年颁降凡例》“诗文”条云:“自前代至国朝,词人题咏山川景物,有关风俗人事者,并收录之。”这里专门强调收录的诗文作品须有关风俗人事,但对于收录诗文的次序、首列文体以及收录重点却并无规定。《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云:“诗文先以圣朝制诰别汇一卷,所以尊崇也。其次古今名公诗篇记序之类,其有关于政教风俗,题咏山川者并收录之。浮文不醇正者勿录。”这里,在继续强调收录诗文须关政教风俗的同时,特别对“制诰”类文体要求首列并单独成卷,显示明代方志艺文志编纂对诗文收录政教色彩的不断强化。同样,这里也没有对“制诰”文体之外诗文的收录次序及重点作硬性要求。清代,中央政权对方志编纂亦十分重视,雍正等有颁令全国各省纂修通志,特别是为了《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要求各府州县及时新修方志。清代方志编纂,对诗文作品的收录,其大体原则与明代一样,如前文所引雍正六年修志上谕,重点强调的是有关政教风俗。又如清代康熙《陕西通志》凡例:“艺文自当依代顺序,但御制为本朝大文,故列于古帝王师相之前,尊君父也。艺文佳篇充栋,今之所选,皆兰台、石室秘笈,宁约勿博,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本,皆在孔门六艺之科,此志书分类之意也。奏议关系最重,非有宣公之心,不能为宣公之言,今于前代奏疏后,即缀本朝本省奏议,谓其心有一揆,许以先后接踵尔。”此明确要求将“御制”首列且单独成卷,显示清初方志编纂的尊崇中央王权之政教意义,与永乐十六年(1418)颁降志书凡例要求“制诰”首列且单独成卷的目的完全一致。但清初方志编纂,同样没有对诗文收录的次序以及收录作品的重点作硬性规定。故清初最早编成的《陕西通志》《河南通志》均在首列“御制”之后,紧接着收录的是诗、赋,而散文类文体均排在诗歌类文体之后。其实,明清方志编纂,虽然有朝廷统一编纂体例要求,但对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收录顺序,以及首列文体、收录重点等也没有固定,故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的诗文收录情况也存在复杂多样性。但若对比同一区域前后编纂的方志,可以发现其中诗文收录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向,即由先列诗歌,后列散文的次序,逐渐改变为先列散文,后列诗歌,且散文的收录,也逐渐固化为首列敕谕诏诰等御制类作品,而其余收录均多以奏疏、记类等为重点,且数量明显绝对超越其他散文文体。
云南地区的几种省志,从明至清,发生的变化是:其一,诗文次序发生互换,由明初的诗歌在前,散文在后,逐步变成散文在前,诗歌在后。其二,逐渐固化成首列御制,先列散文,后列诗歌的体例。其三,收录敕谕、奏疏、记类等数量明显增多。奏疏、记类等文体都是政教色彩最强的文体。此体现的是方志编纂政教思想的强化。故康熙《云南通志》“凡例”说:“艺文首重诰敕、奏疏,次则取大兴除、大建置有关国计民生,可为滇之法戒者登之。若杂文诗赋,惟择其言尤雅者,以畅流览之情,鼓风雅之致。其或无关于滇,虽工弗录。”该志《艺文》也说:“今采有关政教者咸备录焉。”四川地区方志收录诗文的变化与云南基本一致。贵州亦然,无论是省志,还是府志、州志,诗文收录的次序都发生了从先诗后文,到先文后诗的变化,且逐渐固化为首列勅谕,次列奏疏、记类等散文,后列诗赋的模式,并且这种编纂思想在民国时期仍然有较大影响,故民国《余庆县志·艺文志》说:“奏疏议论,未尝不炳炳烺烺,一挥万言,皆经世之文,历千载而不磨灭也。……至里巷歌谣,有关乎世道人心者,轩之史卒皆採择,以觇一时之风化,则艺文志胡可阙!”
贵州方志艺文志先文后诗的编纂变化,大约在明代后期方志编纂中开始逐渐突出。例如,嘉靖《贵州通志·艺文志》文体编纂的次序是:诗类、序类、书类、赋类、文类、赞类、跋类、歌类、谣类、疏类、颂类、记类、墓表类(含挽诗)。不难发现,这种编纂是诗、文混杂,记类收录38篇,在散文文体作品中最多,却被放在最末,而将文学性最强的诗类作品摆在第一位,足见当时省志编纂者政教意识不是很强烈。这种现象,在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的编纂中发生明显改变。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文体编纂次序是:记上、记下、传类、序类、解类、赞类、引类、书类、文类、檄类、疏类、跋类、语类、铭类;诗类、赋类、颂类、歌类、行类、谣类、箴类、夷字演、书籍录。与嘉靖《贵州通志》相较,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编纂的明显变化有:其一,将反映社会治理记录与成效的记类文体升至第一位,且收录数量达到98篇,远远超过之前的记类文体数量。其二,将原来排在第一的文学性最强的诗类文体及其他韵文文体放置在了最末一卷,而将其他反映社会发展的散文文体均置于前面,且散文归在一起,韵文归在一起,足见万历《贵州通志》编纂者政教意识的显著增强。万历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治理出现重大问题,尤其是播州杨应龙之乱,产生巨大社会政治影响。明代统治者对西南地区政治管控明显加强,万历《贵州通志》的编纂充分反映这个时期的边疆治理方略,显示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互动。其后,康熙、乾隆时期,朝廷对西南地区政治管控空前强化,改土归流逐步完成,而相应的康熙、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文体编纂,也将政教色彩强烈的敕谕、奏疏等散文文体列在前面,而将诗歌等韵文类作品列在后面。显然,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散文文体作品的次序、类型和数量的嬗变,蕴含深刻的政教内涵。
明代后期政治衰败,特别是西南地区社会动荡,战乱较多,中央政权要强化政治管控,故方志艺文志编纂将直接反映政教的散文文体置前,体现方志编纂服务政教的思想,也充分体现方志艺文志编纂的治边思想。故万历《铜仁府志》“凡例”说:“艺文,有关经济,中机宜,或忧时述事,读之可以感人,或触景兴怀,咏之可以警俗,虽连篇累牍,不厌备书。若徒雕章绘句,无补民风者不录。”卷12《艺文志》亦说:“铜地虽僻,而冠盖颇来,题咏亦富。大之经国忧民,细之感时触事;远之吊古祝厘,近之陶情写性,皆可以兴,可以观,其于教化之助,裨益良多。”通过方志艺文志编纂有助教化、裨益政治的目的十分明确。而乾隆《云南通志》卷29《艺文》亦云:“至于汉唐以远,诰谕献纳之作、纪时述事之章及昭代公卿大臣讦谟远猷,下逮文人学士之吟咏,择其有关治道人心风俗者,各以类从,编诸简册。”以上下层级区分诗文,将诰谕献纳、纪时述事之章及昭代公卿大臣之讦谟远猷视为上层,而将文人学士之吟咏视为下层。此充分说明自明代万历以降,方志艺文志通过诗文编排顺序改变,以及收录重点的调整,以强化史志编纂政教指归。贵州方志艺文志散文文体的编纂,无疑正是这种方志编纂思潮的产物。
结 语
贵州方志艺文志中散文文体作品的编纂,显示边疆史学发展的特点与成就,蕴含丰富的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首先,呈现出史学与文学的紧密互动。当某一类文体因自身繁荣或史志编纂者的政治需要,则相应得到方志编纂者青睐,收录的数量相应增多。当某一类文体因时代发展逐渐衰落,则方志艺文志的收录数量会相应减少,甚至不收录。其次,呈现出史学、文学与政治交融互动。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贵州方志艺文志收录的散文作品,与贵州地域政治文化紧密相关,是贵州政治、历史、教育、文化的充分反映。同时,随方志艺文志中所录散文作品的传播,其对社会政治能够产生一定影响作用。再次,呈现出浓郁的西南边省地域文化特征。贵州为西南僻壤,居住的少数民族众多,其方志艺文志收录的散文作品,不少反映历代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措,涉及区划设置、军事战争、文化教育等,充分显示了历代边疆治理的方略与特点。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来源:地方志研究
作者:谭德兴(贵州大学文学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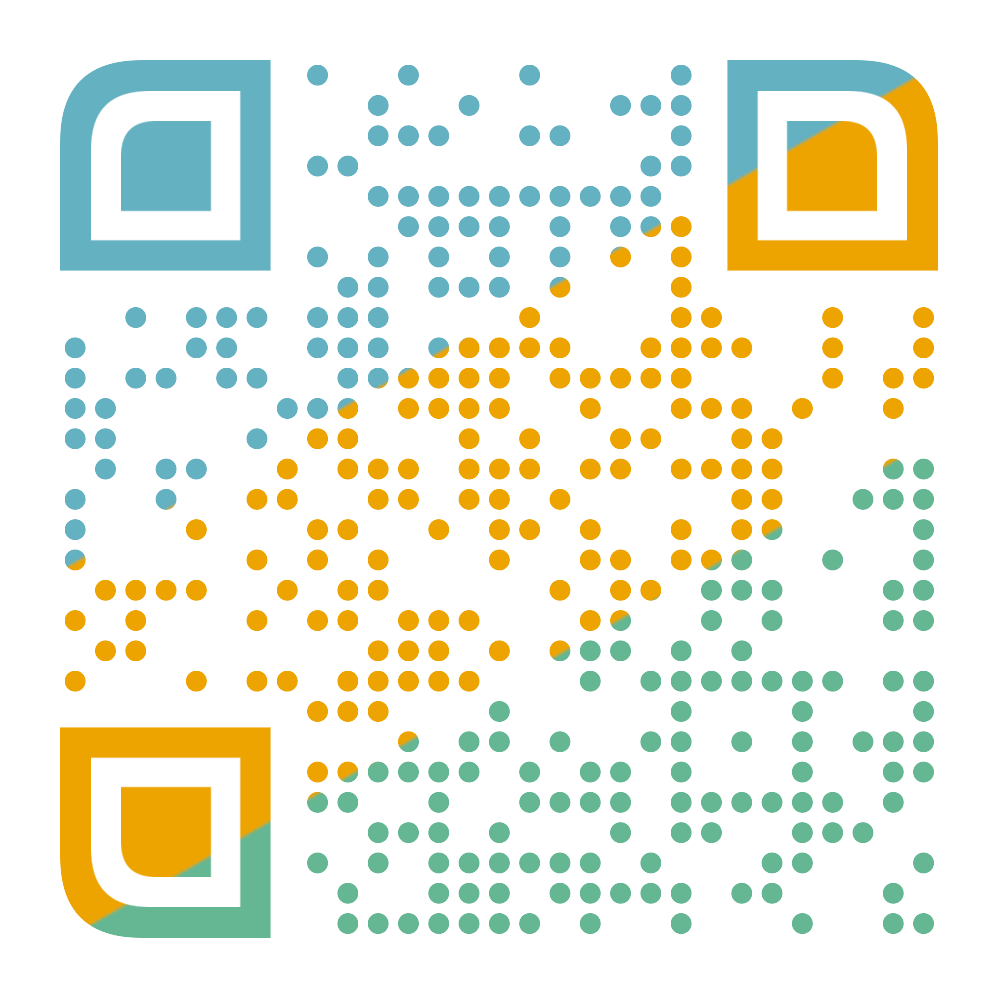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