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秧歌三曲‖罗学娅
秧歌三曲
罗学娅

做秧田
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下乡到了川东南缘丘陵地区的一个小山村。这里不通公路,不通电,连有线广播都没有,非常闭塞,自然也就十分贫困落后。
丘陵地域的山不高,但连绵不断,除了坡,就是沟。大多村庄的农活,不是上坡种包谷、洋芋,就是下沟割草喂牛。同学们都说我运气好,分到了全公社最好的一支生产队——八大八队,那是全公社唯一的一片“平坝”,公社大院和学校,都在我们生产队的辖区,可以说我们生产队是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凡事有利便有弊。正因为这方平坝田多土少,一年四季的农活,基本上都是泡在水田里,这是很多姑娘、大嫂都不喜欢的。
我下乡的时间是在5月上旬,下乡的当年,栽秧子、薅秧子,割谷子、挑谷草等农活都干过了,就是错过了做秧田的机会,觉得是个遗憾,所以,早早就跟队长说了:明年做秧田,一定要叫上我。
下乡第二年,刚过完春节不久,队长就开始念叨“春分前,做秧田”。还在去年点小春的时候就定了:把他家门前那块四四方方的水田,留起来做秧田。
当时,我还想:上好一块田,空起来长浮萍水草,太可惜了。
队长却说我不懂,要是种了小麦、油菜,做秧田的时候还不能收,那才可惜了呢。若要等收割了再做秧田,又误了育秧时节,损失会更大。再说,那些浮萍水草,到做秧田时,正是上好的秧田底肥。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那天早上,队长叫了四五个男社员做秧田,还真没忘记叫上我。
到了队长家门口,大家把鞋子脱了,把裤脚高高地挽在膝盖以上。天气实在太冷,一个二个又都把手插在袖筒里,缩手缩脚地哈着气,迟迟不肯下田。队长进屋拿出一瓶白酒,叫我狠劲地喝两口,暗示我快跳下去。
喝了队长的酒,我只得咬紧牙关,挨着田坎边边梭下水田,一连几个寒颤,刺骨的冷,至今难忘。
没想到,我刚一下田,队长就发话了:人家女知青都下去了,我看你们一个个好不好意思。
大家笑着把队长的一瓶酒喝完了,才纷纷跳下了水田,动作比我利落多了。其实,十多天前,我就看见队长把这块田的水放了,把浮萍水草连根拔起,踩进土里,然后耕田,再灌满水。现在,估计那些水草已腐烂成肥了。
做秧田的工序很简单,首先是耙田。用犁耙将整块犁过的田耙平,将凹凸不平的泥土弄碎。这犁耙有1米多宽,下面是一排粗壮的木齿。两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扶,都得用很大的力气。队长叫我记住做秧田的四个标准:“平、实、光、直”,还叫我先在田边上看,一会儿再叫我干活。
我只能听从队长的安排,乖乖地站在田边,看着他们来回把田耙了两趟,很快就把露出水面的泥土拉到了低处,凭肉眼看,一块大田很快就整平了。第三遍队长叫了一个比较胖的人坐在犁耙上,这下子就拉得更吃力了,除了把泥土压“实”,坐在犁耙上的那个人,还得把田里的草根杂物收拾干净。这样来来回回,不但把水田的泥土做实了,还把整块大田收拾得干净光鲜。
接下来,队长从怀里掏出一根草绳,叫我牵到一头,他牵着另一头,其他人用手沿着绳子牵出的直线掏泥巴,掏出一条条边沿垂直的小水沟,把一块大田分成了若干块矩形的小田。
最后,两个人分别站在一小块田两边的水沟里,抬着一根很直的竹竿,他们叫“耥竿”,从头到尾再把田土耥平,来来往往、仔仔细细好几趟,直到把秧田耥得平平展展为止。
看来,这个做秧田的活儿,还真是个细活儿。六七个主要劳动力,干了整整一个上午,才把这块秧田做好。
队长下午就安排几个大嫂在生产队保管室孵秧。她们在拌桶底垫上稻草,将浸泡了一天的谷种倒入拌桶,再盖上稻草保暖,然后,早晚各浇一次水,如遇天气太冷,她们还要在冷水里加上一些热水,提高一点水的温度。待到谷种露出白芽,就选一个晴好天气“落谷”。
“落谷”更是个技术活儿,得经验丰富的老农来做。他们站在秧田的水沟里,左手挽着装谷种的箢篼,右手熟练地抓出一把谷芽抛出去,一道道很美的抛物线,就把谷芽均均匀匀地撒落在秧田里,再用同样的方式,撒上一层稻草灰。不到一个星期,绿茸茸的秧苗就长出来了,一块偌大的秧田变得越来越充满勃勃生机。
因为做秧田,我还得了个大表扬呢。队长在公社春耕总结会上,得意地说:我们队的知青“鸭儿”(我名有娅),每天天不见亮就在水田头板(扑腾)起,展劲(努力)得很。
很快,这句话就在全公社传开了,成为大家调侃我的经典话语,我还因此落得个“鸭儿”的绰号。

学插秧
40多年前的那个5月中旬,我爬上了煤矿的解放牌大卡车,在一片欢庆的锣鼓声中,离开了生我养我的义大煤矿,下乡到了川东南缘的一个偏远小山村。
第一次出工,就听队长吼:立夏小满正栽秧,双抢节气,耽搁不得,天晴收大麦,落雨栽秧子,一天都不要歇。
火辣辣的赤阳下,收了两天大麦,果然下雨了,晚上还响了几声大炸雷。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长就敲钟喊出工了:女同志到方家冲田栽秧子。
小雨一直下着,我戴起下乡时带来的草帽,急匆匆出门,深怕落后。队长的女儿英英叫住了我,给我披上一块稍作裁剪的白色塑料布,说这个比蓑衣更轻便。到了方家冲田,早已有十来个披蓑戴笠的大娘大婶站在田埂上了,正嘻嘻哈哈地等着大叔们送秧子来呢。英英趁机问我:栽过秧子吗?
我如实回答:没有。
她鼓励我:没关系,一看就会,很简单的。
说话间,队长和几个大叔挑着秧苗来了,只见他们迅速将谷草扎好的秧把子一把一把均匀地抛向平整好了的水田里,一条条穿过细雨的绿色抛物线,瞬间把我带进了“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móu)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的《插秧歌》画面。
“栽秧子喽”,队长很有仪式感的一声大吼,打断了我的遐想,急忙和早就把裤脚卷得老高的大娘大婶们一起,轻轻跳下水田,一字排开,就像事先排练过的一样。我下意识地紧挨着英英,学着她的样子,开始了生平第一次插秧。
“左手握,右手分”,参照英英的示范,我左手捡起一个秧把子解开,拇指顺势拨松3—4棵秧苗,右手迅速接过,拇指握住秧苗,掌心护着苗根,食指和中指夹住秧苗根部,垂直插进稀泥,窝距大约两拳。一人一般插5—6窝,鉴于我是初学者,英英叫我插4窝。第一排,4窝插完,刚一后退,就浮起来2窝。“插浅了”,英英叫我捡起浮起来的秧苗,重新补插。
我怕再插浅了,特意用力一插,又比插好的两窝秧子矮了一截。“深了”,英英叫我把握好插入三分之一的尺度。还好,我的左右手配合还比较协调,很快就掌握了插秧的基本要领,虽然株数和行间距都还不很均匀,插得也有些歪歪扭扭,但英英却说鼓励我:对的,就这样一排一排地插,插完一排退后一步,不要乱退,以免伤着秧苗和踩烂田泥。
教了我,她就埋头追赶已经退行很远的大娘大婶们去了。这时,我才抬头看了一下大局面:10多个大娘大婶,个个都铆足了干劲,你追我赶,几乎保持在一条线上,刚才明镜似的一块大水田,已有一小半穿上了绿衣裳。刚入土的秧苗,横看成排竖成行,只有我栽的这4行,有点不顺眼。
我不敢耽搁,弯下腰,弓着背,鼓足劲,继续插秧、后退。
不一会儿,大娘大婶们陆续上田坎了,英英远远地在我身后倒插过来接我。
田坎上亮起一个大嗓门儿:“关猪儿喽”,接着就是一阵大笑。原来,英英接上我了,我被关在了水田中央。英英随手把我插歪了的秧子纠正了几窝,然后叫上我,小心翼翼上了田坎。
她故意在大伙儿面前表扬我:第一次栽秧子,就能栽成这样,能干。
大伙儿也七嘴八舌地跟着夸我能干,是个干庄稼活的料。
我知道大家是在鼓励我,但看见一大块水田,这么快就在我们的指尖下换上了绿装,一份栽种的喜悦和丰收的期待油然而生,让我铭记住了那个学会了插秧的小满节气。
忙薅秧
“芒种忙忙栽,夏至谷怀胎”,这句农事谚语,很小我就会诵读,但并不知其意。下乡后,才发现生产队的男男女女,大多会念这些谚语,而且很多都是我下乡前从没听过的。
我是5月中旬下的乡,小满插秧时,队长就开始念叨:“芒种不种,过后不补”,叫大家一定要抓紧在芒种节气之前,把秧子栽完,过了芒种栽的收成就不好了。
我落户的村庄是丘陵地域,虽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大家说的平坝,但仍没有大块成片的水田,一块一块不大的水田,弯弯拐拐绕着山转,呈不规则的梯田状。如果是顺着一条沟、由低到高的田,就叫冲田,得用水车把水从低处的田一层一层地冲到高处的田里去,才能保证秧苗不缺水。
20多天前栽下的秧子,经几场初夏的雨水一浇,眼看着嫩绿的秧苗就蹭蹭地往上窜,一派绿茵,错落有致,微风一吹,碧浪满山,煞是喜人。
我们生产队长是一个土改时期的老干部,更是一个干农活儿的好把式,什么节气该干什么农活,他心中有数、倒背如流。
芒种那天,他一大早就吼起:“薅秧子喽,秧子薅得好,如上肥料草”。
我是第一次薅秧子,路上,英英就给我讲:秧子要薅三道,头道最重要,需特别仔细,把秧苗周围的泥土薅松,刚长起来的小杂草薅进土里,长出来了的杂草和稗子要连根拔掉。这样,秧苗才长得快,长得好。
我习惯性地紧挨着英英下了田,先用右脚绕着右边的一窝秧苗薅一圈,再用左脚把左边的秧苗薅一圈,左右交叉,一排薅4窝。在薅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夹杂在秧苗中的稗子和杂草扯掉。
上学时,老师就常常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要学工学农学军,绝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真别说,初下秧田薅秧子,我根本就分不清秧苗和稗草。英英拔了棵稗子给我看:“稗草叶子上的茎是白色的,叶子摸起来光滑没毛”。还在我手臂上扫了几下,让我感受一下。
我自认为一下子就学会了,不但能分辨出秧苗中的稗子和杂草,还很快就学会了薅秧子,感觉比插秧简单多了。
不一会儿,就薅完了一块田,大家纷纷上了田坎,看见很多人都在“噼噼啪啪”地拍小腿,英英叫我也快拍拍,害怕有蚂蟥粘在腿上。我拍了几下,没看见有东西掉下来,刚要走,英英叫我别动,她发现我左小腿后面粘着一只蚂蝗,便用手指掐住它,生生地扯下来。我看见蚂蝗被扯掉后的伤口流出了鲜血,吓得惊叫。英英叫我别拍,吐了一泡口水在伤口上,揉了几下,说“没事儿了”,我也就真不怕了。
薅秧子虽不是体力活儿,但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的,特别是两条腿,就像经历了长途跋涉一样酸痛。
头道秧薅完了,紧接着又薅二道秧,越薅越感觉轻松了许多。现在想起来,最恼火的是薅第三道秧子,那时秧苗已长到齐腰深,茎秆粗壮,叶边就象有锯齿一样,割在手臂上满是红一道白一道的口子,又痒又疼。
遇到晴天的下午,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头上,尽管戴着草帽,也晒得浑身滚烫。田里的肥水,被我们的双脚薅得臭气熏天。直到现在,都还忘不了那个烈日下在水田里薅秧子的艰辛。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做秧田和插秧都用上了机械化,栽好秧苗的秧田,早就使用了稻田除草剂,再也不用人工薅秧子了。
40多年前的春分、小满,到芒种,我历经了做秧田、学插秧和薅秧子的全过程,印象极深,感受颇多。今天,我用拙笔把它们记录下来,希望能留住那远去的秧歌三部曲。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罗学娅(泸州市作家协会、内江市作家协会会员)
配图:方志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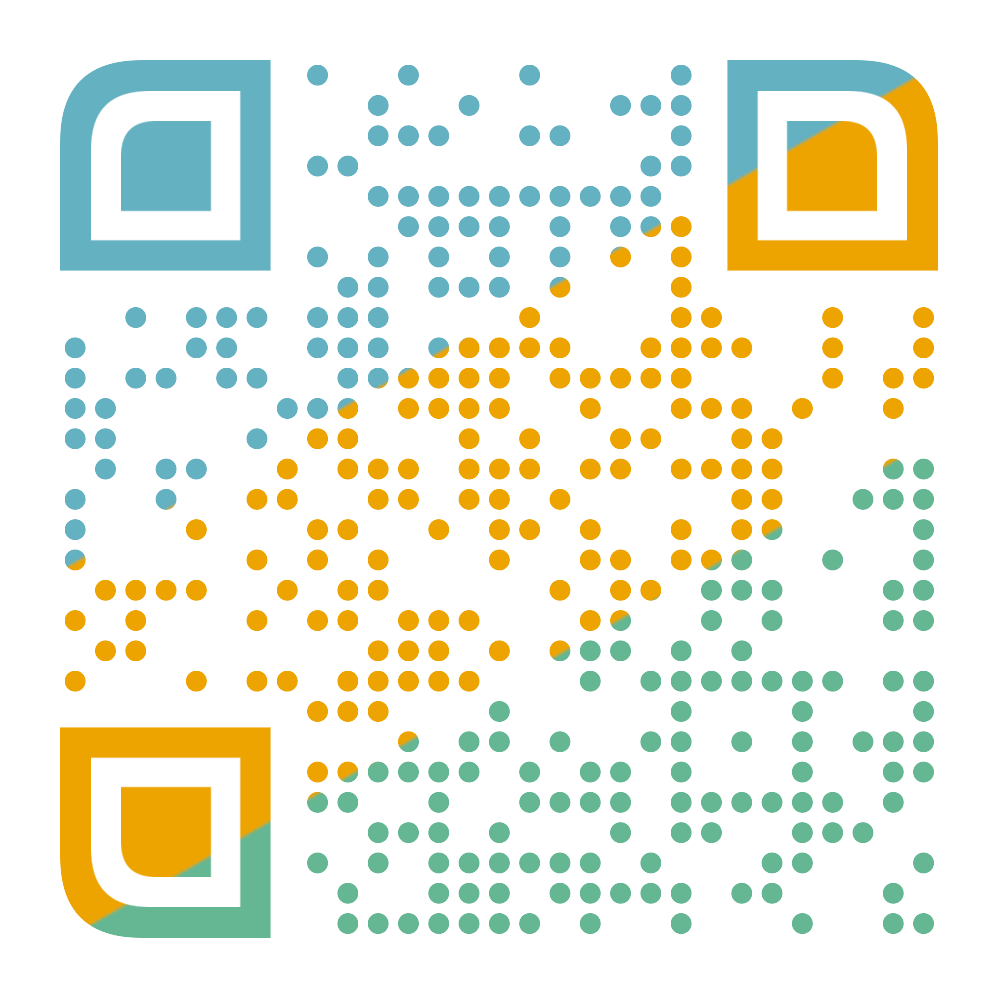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