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历史文化】丁伟 ‖ 晚清大佬与四川书院
2016年,四川大学建校120周年。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从尊经书院到四川高等学堂,从存古学堂到四川国学院,从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到国立四川大学,从华西协合大学到四川医学院,从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校并立到经过战略合并的崭新的四川大学,百川成海,涵乾纳坤,岁月的沧桑凝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胸怀铸就川大的百年辉煌。如果说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心脏,那么四川大学图书馆自建校伊始就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如今图书馆中收藏古籍线装书近三十万册,民国期间出版的报刊杂志也颇具规模,原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毕业生论文则是本馆另一重要特色资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籍特藏资源既是前贤遗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百年川大风雨历程的见证。本文通过史料钩沉,试图从古籍汇聚的角度,再现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百年历程。
锦江书院 层次最高藏书颇丰
考察国立四川大学的藏书史,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两所书院——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
锦江书院是四川历代书院中层次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办学最典型的书院。书院设立于清初康熙年间,自开办之初即设有藏书之室。《锦江书院纪略》记载,咸丰八年(1858)监院李承熙对院中藏书进行统计:原有藏书仅24种197册。此后地方官员多有捐置,嘉庆十年(1805)四川布政使董教增捐发改定书籍7种159册,嘉庆十八年,荆州知府洛昂捐置书籍法帖26种1293册;嘉庆十九年,四川布政使陈若霖捐《钦定学政全书》2套;嘉庆二十四年,盐茶道奇成额捐发13种670册。
光绪二十八年(1902),锦江书院被裁撤,藏书一并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只是锦江书院的藏书几乎没有印记,分散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很难被辨认出来。锦江书院发展到后期,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于是尊经书院应运而生,主其事者即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十二年六月,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任四川学政。光绪元年,协同四川总督吴棠创办尊经书院,培育蜀中英才。因为川省地处偏远,购书不易,张之洞率先垂范,捐俸从外地购书二百余部数千卷,存于书院尊经阁中。因为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故其所捐赠书籍均钤“提督四川学政南皮张之洞捐奉所置书”朱印。
张氏所置书,经史子集,四部俱备,如《皇朝祭器乐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揅经室集》等,均为切实有用之书,符合张之洞“通经致用”的一贯育人主张。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做学问?如何修行个人品德?当时学子大多心存疑惑,有感于此,张之洞亲自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为书院诸生答疑解惑。即便在今天,这两种学术著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育仁
此后,尊经书院历任山长如王闿运、伍肇龄、刘岳云、宋育仁等均十分重视藏书。光绪二十三年,宋育仁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与廖平、吴之英倡导维新思潮,尊经书院成为四川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宋育仁曾一次性购书103种,1040册,舆图3部18张。

尊经书院旧照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籍大部分都是介绍西方政治、历史、经济、科技的西学著作,尊经书院藏书格局从单一的国学旧籍逐渐走向多元化,院中诸生眼界日趋开阔。
古学堂 谢无量任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下令裁撤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院时代走向了终点。次年五月,原尊经书院监院薛华墀、教谕罗彤将这一批书籍清点造册,移交给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学堂。宋育仁当年采购书籍的清单,今天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四川大学档案馆中。

岑春煊
宣统元年,清政府要求将设立存古学堂作为各省“筹备立宪”的一项内容,四川总督赵尔巽邀请五十一岁的清流名士赵启霖,入川主持四川存古学堂筹办事务。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瀞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弹劾段芝贵与庆亲王父子一案颇具声望。
赵启霖于宣统元年(1909)旧历四月十三日抵川,上任之始即着手整顿学务,并上《请奏设四川存古学堂折》。得到批复后,赵启霖拟定存古学堂章程,同时聘请谢无量任学堂监督,华阳徐炯(子休)、名山吴之英(伯朅)为教员,学堂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掠影
因为“学务多束于部章,鲜有实济,又因先母年近八旬,思归心切”,宣统二年,赵启霖即请辞去提学使职务,并于同年二月获准。离川之前,赵启霖自捐四百元,购置图书,供存古学堂诸生研读。这批古籍首页均钤“提学使赵捐置”朱印,具体数量尚待统计。

晚清时期的锦江书院
张之洞之创办尊经书院,赵启霖之筹设存古学堂,前后两任提学使在蜀学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前贤已逝,他们捐置的书籍,却传之久远,嘉惠后学。辛亥革命后,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后并入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院以整理四川文献、搜集国史文献、编辑光复史为主要任务,因此大批购置国学典籍。此一阶段的藏书,《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概况》一文略有涉及,“明板册府元龟、六朝诗纪、补续全蜀艺文志等系谢无量在国学馆时购置,明板经学及东医宝鉴等则廖季平先生所置”。国学院、国学馆的书籍均钤有“四川国学院(馆)所藏金石图书之印”,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中占据很大比例。
古籍甚丰 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
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并入四川中西学堂,后来演变为国立成都大学,存古学堂则并入四川国学院,逐渐演变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再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至此,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所藏书籍以及刻书板片实现合流,全部进入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国立四川大学时期,学者推荐购买也是图书馆文献建设的重要途径。此类书籍,内封页均有铅笔小字一行,“某某介绍”。如文院蒙文通介绍之《印度札记》,文院赵少咸介绍之《集韵声类表》《魏书校勘记》《淮南旧注校理》,文院周癸叔介绍之《梅村诗集笺注》《问字堂集》《后汉纪》,文院丁山介绍之《集韵考证》,均是此例。抚摩遗编,心生感慨,先辈学人在书籍上留下的雪泥鸿爪令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始觉大学之大,不在广厦,而在于大师,在于底蕴。此外,民国期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排印或者石印出版的教材,也构成了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的一部分,因其流传不广,存世稀少,因此弥足珍贵。

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掠影
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另一重要源头是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与国立四川大学的发展脉络不同,华西协合大学自建立之初就比较稳定,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来源相对比较简单。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成立于民国三年,初期收藏不甚丰富,且多以西文书籍为主。为充实馆藏,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程芝轩曾向罗氏好一斋商借25000册中文古籍寄存馆内,以满足教学科研的需求。
民国二十年,华西协合大学得到哈佛燕京学会的三十万美元用以发展本校东方文化研究事业,校方在息金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作购置图书及设备。《华西协合大学校刊》记载,1938年暑假,图书馆中文部在北平各大书局一次性采购中文古籍120多种,到馆书籍均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并参考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
据统计,截至1945年,馆内收藏中文图书137199册,就收藏数量而言,以四川方志为最多,次则为钞本及名人手迹,如顾印愚、李榕(申夫)、窦垿(兰泉)等人遗墨均赫赫有名。以版本而论,馆藏元代刻本2种,明刻本30多种。1949年,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又一次大规模收购中西文古籍,数量不下千种,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这是今天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部敦煌写经。1951—1952年间,图书馆又接收唐棣之、曾彦适等人所捐线装古籍一万多册,馆藏资源得到进一步扩充。
刻书事业 一度元气大伤
雕版印刷,是中国传统书籍的主要生产、制作方式。四川曾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刻书重镇,与浙江、福建鼎足而三,并称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历史上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即刊刻于成都,南宋时期《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眉山七史”等大型书籍的刊刻,续写了蜀中刻书事业的辉煌。然而历经蒙古铁骑南侵和明末张献忠的报复性屠戮,曾经富庶的天府之国社会经济遭到重创,传统刻书业亦随之陷入低潮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才有所改观。

尊经书院刻本
乾隆年间,成都地区已经产生很多刻书铺,其中以江西人开办的店铺名气较大。嘉、道以后,成都地区的刻书事业日渐繁荣,刻书店铺不胜枚举,这里仅就与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密切相关的成都官书局、锦江书院、尊经书局以及四川存古学堂略作稽考。

四川高等学堂的自修室
成都书局成立于同治年间,曾经刊刻《相台五经》《御纂七经》《经典释文》、殿本“前四史”、《新五代史》等一大批经史典籍,字大板朗,刊刻精细,可称之为上品,成为当时士人学子争相购买的对象。成都书局结束的具体时间不可详考,但是其刻书板片的下落却有迹可寻。同治十三年,曾任礼部左侍郎的四川兴文人薛焕联合全省十五名颇具声望的官员学者上书四川总督吴棠、提学使者张之洞,倡议建立书院,培养蜀地人才。光绪元年春,尊经书院成立,张之洞为此撰写《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拟定尊经书院章程十八条,第十七条为“惜书”,其中提到,“局刻书板藏于院者,印售时视纸料定价三等”。其“局刻书板藏于院者”当指成都书局所刻书板。
尊经书院 多以经史词章为主
尊经书院成立之初,诸事草创,百废待举,并没有成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来主持书籍刊印工作。为了满足教学需求,书院零星刊刻一些经史小学类著作。比如刊刻于光绪元年的《经典释文》,即是由薛焕提供底本、吴棠筹资刊刻,是尊经书院早期刻书的代表。这一时期,尊经书院的刻书经费来源不稳定,刻书难成规模,但为日后的刻书事业提供了人员储备与技术积累。

王闿运曾任尊经书院山长
光绪四年,经学大师王闿运应邀来川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次年六月,王闿运与孙任谋划设立尊经书局,指定斋长负责书局的日常刻书事务,经费从省府库中划拨。从此以后,尊经书院的刻书进入全盛时期。据统计,尊经书院刻、印书籍有目可查的,据黄海明在《概述尊经书院的刻书》一文中统计,大约99种(含丛书2部,若将子目视为单种计,为119种),1912卷,22703块书板。尊经书院刻书多以经史词章为主,也有少数科技类书籍和反映维新变法新思想的进步书籍,由于品种丰富,校勘精审,质量上乘,深受士人学子追捧。内封或者刻“尊经书局新刻”,或刻“尊经书院藏板”,或于卷末刻书院学子校勘姓名,或于序跋中有所揭示,这些特征是我们今天辨认尊经书院刻书、印书的重要依据。
书板忆旧 曾存在旧皇城洞中
锦江书院也有刻书活动,不过不及尊经书院的刻书规模大影响深。咸丰年间,监院李承熙对书院所存刻书板片进行清点,并作详细记录:道光十四年,四川总督鄂山捐发书籍板片五种,分别为《新刻日知录》,计板片连同封面共五百二十二块,《新刻日知录之余》,计板片连封面共五十四块,《新刻菰中随笔》,计版片连封面共三十二块,《新刻困学纪闻》,计板片连封面共四百零五块,《新刻小学》,计板片连封面共一百零六块,书板存藏书之室;道光十六年,锦江书院监院朱公澧存家藏书籍《希有录》板片连封面共二百二十四块,咸丰六年监院李承熙补刊,存藏书之室;道光十九年,四川总督苏廷玉镌刻《御纂八经》,计板片连封面共七千九百六十一块,木架十四架,存文翁祠。而《锦江书院纪略》一书刻于咸丰八年,书板也存于书院藏书之室。

国立四川大学大门
存古学堂设立之后,接收原锦江、尊经书院300余种著作的雕版五六万片,在卧龙桥设存古书局,修补原有板片,刊刻新书,廖平著作《六译馆丛书》即为存古书局所刻。国立四川大学成立以后,存古书局的书板移交给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成为校产的一部分。《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一文中介绍,“本校所存木刻书板,共有40155块,由书板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其中有29种14800多块存在图书馆楼下,另外25000多块则因限于经费,存在旧皇城洞中。”
守护三十万册古籍线装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几千公里的海岸线遭到封锁,西方科学类书籍进入中国的渠道被切断。东南地区大片国土沦丧,各省的官书局和印书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传统的国学类书籍也十分匮乏。时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敏锐地察觉到广大学子读书难的问题,向中央政府申请修补书板经费十万元,印刷费用六万元,将馆藏板片择要印刷,第一期印书25种,每种印37部,共计7881册,其中就包括“前四史”“相台五经”等传世经典。所印之书,除满足本校教学研究需求外,还分送中央各部,远销省外。古老的书板又一次焕发了青春,为学术之传承、文脉之延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由于各种原因,四川大学所藏的四万块书板后来仅保存下来两百多块,收藏在图书馆善本室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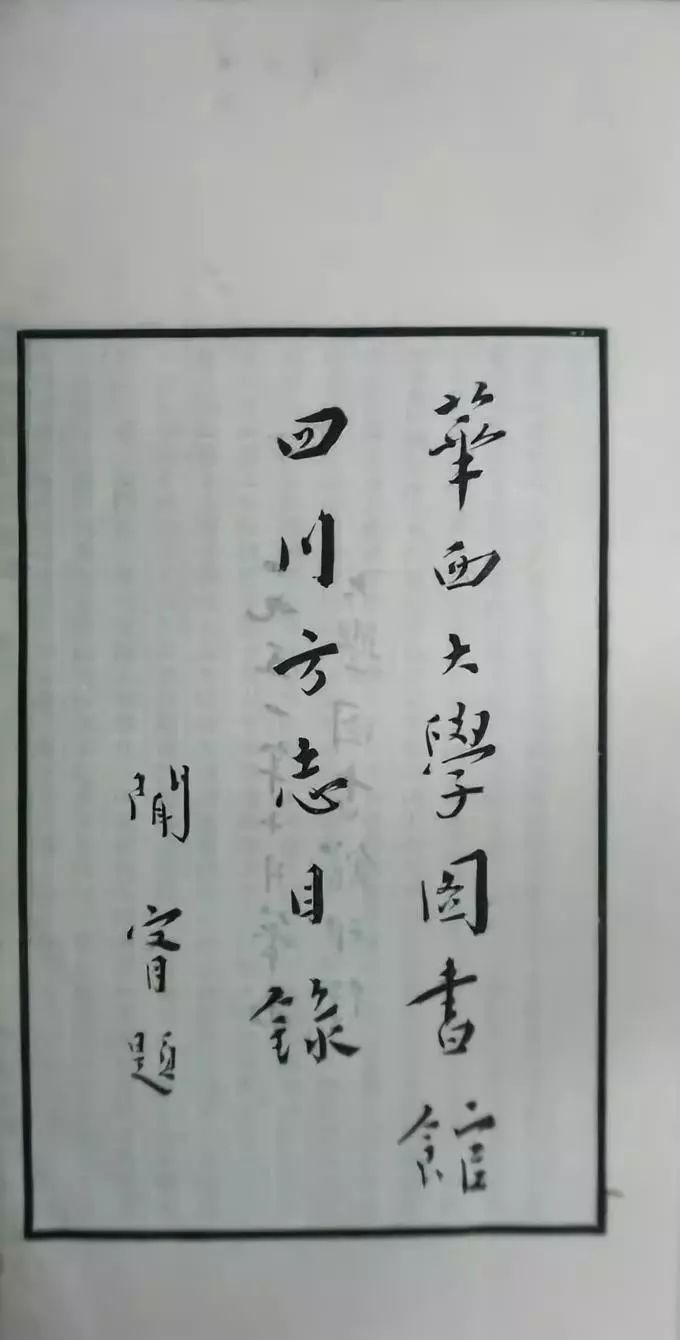
闻宥题四川方志目录
地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人文现象之专书,是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的重要材料。1932年,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曾向全省各县府发函,征集地方志,以补馆藏之缺。经过近十年努力,到1943年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数量已达四百余部,其中包括数十种手抄本各县乡土志,实为孤本。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也十分重视地方史志资料的收集。图书馆成立之初,方叔轩、程芝轩二先生即将地方志征集作为收藏重点,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林名钧、岳清澄二先生极力搜访,得三百多种,四百多部,涵盖四川一百四十多县。其中《嘉靖四川总志》抄于北京图书馆,《营山县志》抄自宁波天一阁,《天启成都府志》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康熙成都府志》抄自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文献征集不易,值得后人珍视。1991年,图书馆对馆藏地方志进行系统清理,编纂《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共收录1949年以前编纂的地方志1213种,1413部。进入新世纪后,四川大学图书馆将馆藏稀见方志影印出版,昔日难得之文献,今朝化身千百,孤本不孤,嘉惠学林,实为值得庆幸之举。

四川大学善本书室书柜
古籍资源既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也是百年川大历史底蕴的见证。对于以科研教学为主要目标的高校来说,古籍一方面要在教学科研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也要得到妥善的保护。作为这三十万册古籍线装书的守护者,四川大学不断加大古籍保护的力度,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设标准化古籍库房,通过对温湿度的精密控制来延缓古籍的衰老速度。此外,图书馆专门成立两百平方米的古籍修复实验室,在这里,传统手段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互融合,千方百计为古籍延息续命,让流传了百余年的前贤心血传之久远,斯文不堕,经典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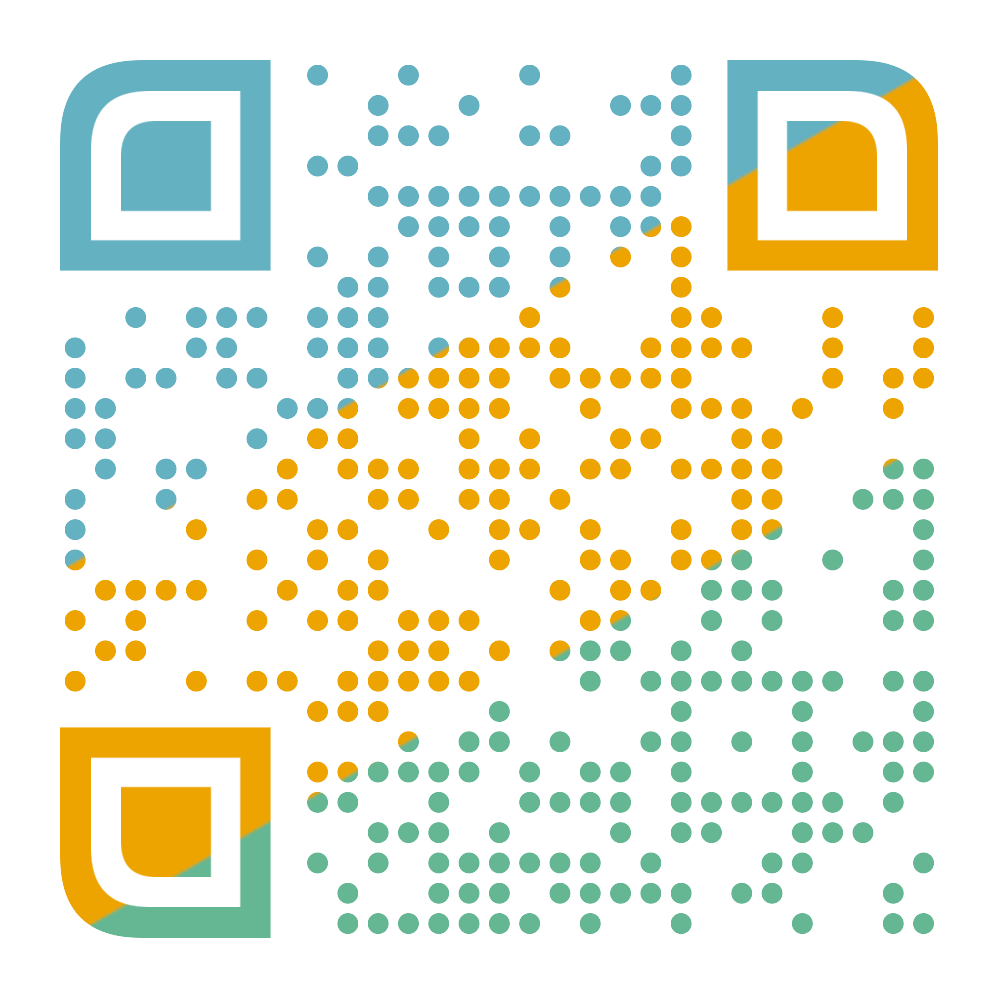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