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特辑】荆姑爷‖申福建
荆姑爷
申福建
2021年春天,荆姑爷长眠在他家旁边的土地里,他可爱的小孙子童言无忌:“爷爷睡着了”。一阵风吹过,树枝唰唰作响,仿佛带来荆姑爷的问候。我觉得他没有去世,而是在静静地守着这个家,守着这片土地。

荆姑爷的父母是佃农,土地改革时分得土地、房屋,1949年出生的他自然有份。每次看到他家光洁透亮的嵌花土漆立柜和装糖的兰花瓷罐,总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盛世修谱,厘清了荆氏家族脉络,荆姑爷上了族谱,多次去荆氏祠堂参加清明会。
不知为什么,在我们老家,姑妈、姨妈均喊嬢嬢,姑父、姨父均喊姑爷,而且要在姑爷前面加上姓氏,荆姑爷就是这样喊出来的。
大嬢与我妈妈同年,我都1岁多了她还没成家。荆姑爷与我家相隔不到2公里,属不同的大队。他们院子的王二爷与我们院子的王幺爷是堂房兄弟,两家的婆婆牵线搭桥,大嬢与荆姑爷见了面。
看亲是在合川县城,妈妈带了我去。一到街上,我就哭闹着要吃甜糕,荆姑爷走了好远去给我买。通过一段时间恋爱,找八字先生合八字、择期,结婚证一扯,酒席一摆,就成了一家人,我也从荆叔叔改口为荆姑爷。大嬢比荆姑爷大3岁,婚后的生活正应了“女大三,抱金砖”。
父亲去世早,两个姐姐出嫁,两个弟弟还小,家庭的重担压在荆姑爷稚嫩的肩上。因此,小小年纪就开始干农活、挣工分,学会了犁田打耙、栽秧打谷。荆姑爷是筋骨人,干活不快不慢,背篼、撮箕、筲箕,农村常用篾器都会编,是我的启蒙老师。煤矿来招工,他把机会让给了二弟。有时喝了酒,话赶话,他也会感慨:“哪哈儿我还是可以去端铁饭碗。”

仅仅小学毕业,荆姑爷算账却又快又准,算盘打得溜溜熟,珠算的三盘清、七盘清、九盘清就是他教我的。那时,他们生产队土地300多亩,人口300多,是一般生产队的2倍。荆姑爷担任生产队的记分员,根据队长安排,喊活路、记工分、分粮食、算劳动报酬、补进补出,分毫不差。后来,荆姑爷当选为队长。

荆姑爷家住在一个大大的四合院,大门外高高的梯坎显得庄重大方,梯坎旁有两棵高高的核桃树,一棵为铁核桃,一棵为米核桃,每年吃新鲜核桃时,我们都会弄得两手漆黑。梯坎左侧高高的堡坎上有个阳台,视野很开阔,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堂屋侧面有两道对称的小门。三道门一关,风可进,雨可进,盗贼不可进。

三弟兄分家,荆姑爷分到间大屋,在院坝里修了简易的厨房和猪圈。每家占一点,那四四方方的石板院坝所剩无几。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已婚知青全家返城,把院子外面自建的房子以300多元低价卖给荆姑爷。荆姑爷家卖了三条肥猪,东拼西凑,一次性付清。看到没出去打工的荆姑爷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就象现在在大城市买房没有贷款,院邻惊得张大了嘴巴,他们给大嬢取了个雅号——“老默”。大嬢回敬道:“你默到好来!不一瓢一瓢喂,猪就长肥了?不一瓜档一瓜档淋,就有菜卖了?”
渝南高速公路从他们院子通过,给了迁建补助,荆姑爷在公路边建起两层楼,开了个小店,卖油盐酱醋、打米磨面......荆姑爷很高兴:“电费还是找得到。”随着城市扩张,周边被环城路包围,他们那儿成为农村“孤岛”。养老金每月按时打在卡里,还可以种庄稼,表妹、表弟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绿树环绕的小院成了货真价实的别墅。

荆姑爷性格随和,从不与人争输赢,比高矮。脸皮薄,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买进卖出都是大嬢。只有在亲朋好友聚会时,几杯酒下肚,论农事,话桑麻,嗓门提高,声音加大,男子汉的气势才得以显现。“我屋的包谷提前了一发水点下去,所以能卖好价钱”“我屋的猪喂的粮食加饲料,所以长得油光水滑”“你那个谷子肥施多了,长莽了”“你那个莴笋秧长得好,我来匀点”......其实,和艺术家一样,农民在一起也会交流、争论,甚至炫耀,不过他们针对的是大地这张“纸”和有生命的“艺术品”。有时喝得说话打啰啰,大嬢气得咬牙切齿:“又喝那么多猫尿,舌头都打不转了。”

在荆姑爷主持下,三弟兄轮流供养母亲,从不扯皮,虽是粗茶淡饭,但也有滋有味,荆婆婆渡过了幸福的晚年。因父亲在外地工作,幺爸身体不好,自我记事起,家里大凡小事都请荆姑爷来帮忙,挑抬犁耙,收粮收食......随喊随到,从无怨言。有次荆姑爷家包了20个皮蛋,马上给我们家送了10个过来。举家到内江后,我们回去,或者他们到内江来,腊肉、鸡、鸭、蛋、新米......每次都是几口袋。

日复一日劳作,荆姑爷很少出远门。1992年,表弟考上四川省建筑工程学校(今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校,荆姑爷去送他。那时常有不良青年偷摸扒窃,带着上千元的学费,荆姑爷大着胆子、小心翼翼把表弟送到位于德阳的学校。表弟上学经济压力大,荆姑爷随我父亲到珠海建筑工地打工,没有专业技术,安排什么干什么,烧水工、保卫,每个月的收入及时寄给表弟和大嬢。

从内陆到海滨,从农村到城市,就象淡水鱼游到了大海,那五光十色让荆姑爷头晕炫目,总觉得缩手缩脚。看不到庄稼、蔬菜的生长,就感受不到季节的变化,没有家禽、家畜的陪伴,就少了些生气,没有院邻天马行空的龙门阵,就少了份乐趣。但他一直忍着,忍到表弟工作,忍到家里有了积蓄,忍到因工程量减少裁人。

当买好火车票,原本同路的工友头天晚上打牌输了个精光,决定暂不回来时,荆姑爷慌了神:“他不回去,我啷楷办?”我们笑他胆小,其实,我们又有多大的胆子?后来又去干了几年,心心念念,总是想家。
脚一沾泥土,没有上下班的时间限制,没有人点名查岗,荆姑爷立马来了精神。看着孙子、外孙吵吵闹闹,荆姑爷有时虎起脸招呼,但舍不得动一根指头;庄稼、蔬菜也有灵性,在荆姑爷的打理下,长得嫩摇摇、水灵灵;猪、鸡、鸭一听到荆姑爷的呼唤,“噜噜噜”“咕咕咕”“嘎嘎嘎”的叫声仿佛在唱欢歌。大嬢曾感慨:“你这样累,一年找得到几个钱?比得上打工哇?”荆姑爷嘿嘿一笑,又做事去了。

十多年前,荆姑爷常喊身上痛,于是每天喝点药酒解乏,渐渐成了习惯。一个烤酒匠上门推销,帮忙烤酒,只收工钱。荆姑爷当即买了高粱来烤,第二年还专门种了高粱。给每个孙辈窖藏了一坛酒,包括我的儿子,他说等这些娃娃结婚时弄出来喝。每次回去,我也会陪荆姑爷喝上一杯,那醇厚的味道才是高粱酒的本味。荆姑爷多次到内江来,我陪他走走看看,陪他喝点小酒,给他买点内江特产,他不直说,看得出他很高兴。

突然背痛,到医院检查,在肺部积液里发现了癌细胞。到大医院治疗,吃各种单方,大嬢尽了全力,表妹、表弟尽了孝道。可是,癌症的魔爪扼住了命脉,在疼痛与不甘中荆姑爷走完了人生。

人生看似很长,但生命回归大自然却不过一瞬。至今,我才理解荆姑爷的故土难离,因为,他属于这片土地,因为,他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有天晚上做了个梦,荆姑爷在杀鸡杀鸭,清理内脏,样子一点没变。我不知道,是您想我了,还是我想您了。清明将至,干杯,荆姑爷!
写于2022年4月4日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申福建(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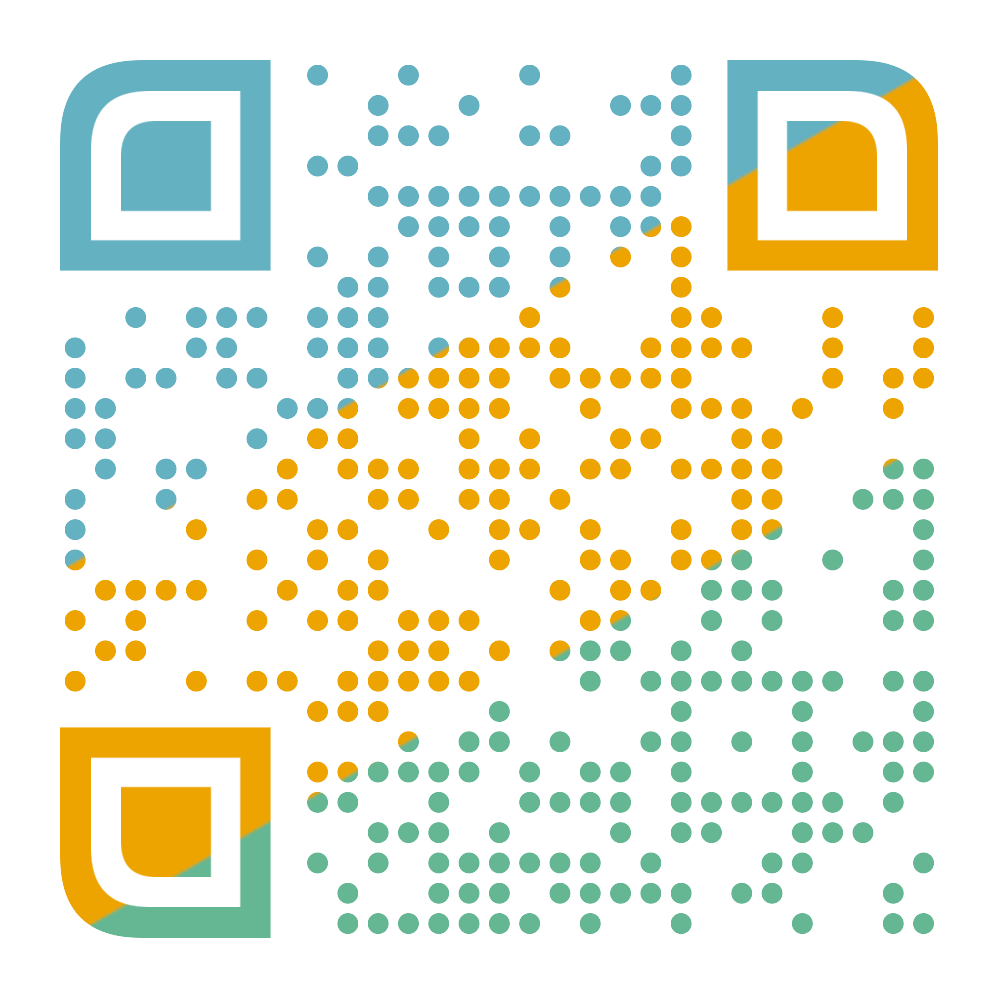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