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序言三篇
《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
序言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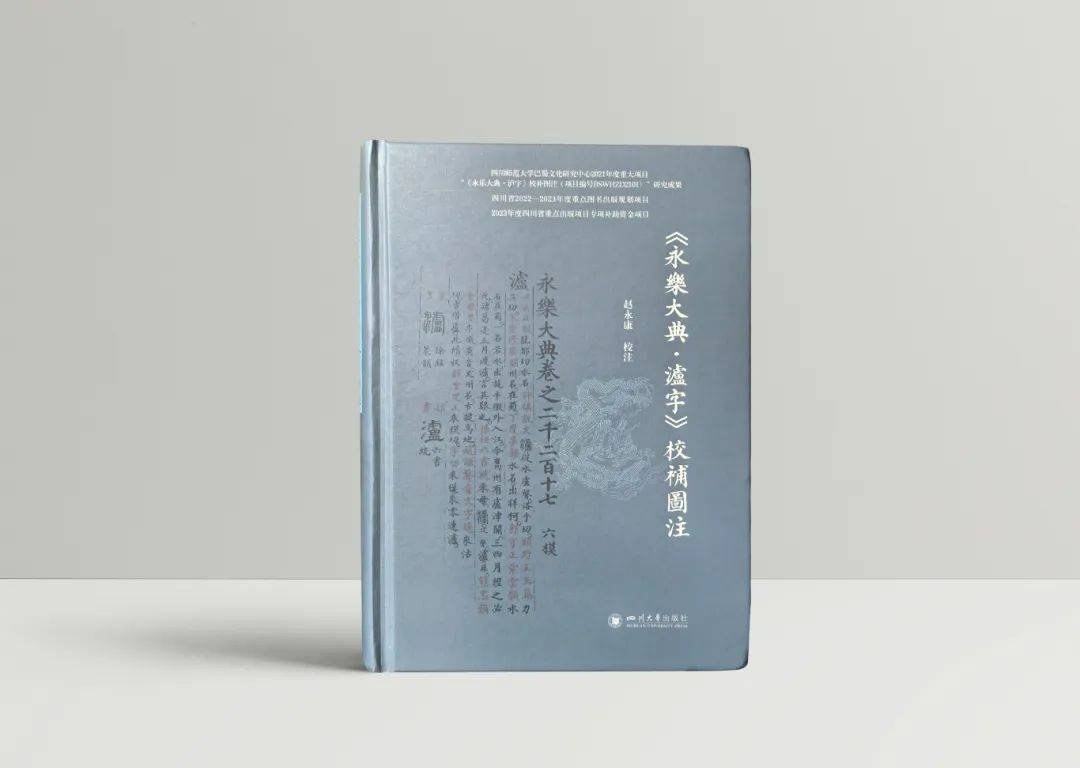
蓝勇先生序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在全世界有重要地位。但是,雕版技术下的原版一旦遗失,再版就相当困难。几千年来,伴随周期性王朝更替的烽戎兵燹,封建统治者和文人的喜恶无常,古代的许多文献难以流传,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巴蜀地区的地方志编纂,在全国地位很高,东汉《巴郡图经》,是全国最早编成的地志,完整保存至今而且最为古老的地志,也是记述巴蜀的《华阳国志》。进入宋代,巴蜀地区又出现了大量的志书,仅在我《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书中统计到的,就将近百种。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珍稀文献散佚殆尽。幸得中国有独特的类书,将其中一些的片言碎语保留了下来。唯一传存的宋代曹叔远编纂的泸州地志《江阳谱》,就是借助《永乐大典》得以残存。不过直到二十年前,学术界对于《江阳谱》,认知程度仍然很低,研究缺失,利用其书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就更少了。《永乐大典》泸字在《江阳谱》之外,还保存着很多我们以前少有利用的珍贵资料。从这个角度看,征文考献,科学、规范、系统地校勘考证笺识《永乐大典》泸字,整理出一个学术价值较高、可征可信、方便学人利用的文本,就特别有必要。
宋代巴蜀方志丧失殆尽,已经找不到任何一种历史文献可以用于与《江阳谱》比校互证。点校笺识《永乐大典》“泸”字下面的历史文献,难度很大。宋代的川南,是汉族与多个族源不同的少数民族交汇之地,民族历史记忆众多,涉及的民族语言、文字、地名等问题,更增添了整理的难度。必需要有熟悉乡土历史,又有专业考、校功夫的学者,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很幸运的是:地产《江阳谱》,天生赵永康。永康先生师出名门,早年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长期研究巴蜀特别是其家乡川南地方历史文化,成果甚丰。由他来点校《永乐大典》泸字,天造地设。
赵先生的这个《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对于相关乡土、城镇设施、地名考释特别精严。历代地理总志,对于乡土地名的记载都比较疏略,特别是明代以前的乡土地名,记载更少。对此,我在《中国近古以来的乡村地名》一文中已多有讨论。《江阳谱》把宋代泸州及其周边区域的地名,系统地保存了下来,这本身就是川南黔北地方历史文化上的一大幸事。但是,经历宋元交替和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文献、文物荡然无存,文化信息大量丧失,乡土地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川南黔北的历史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反映在地名上最为突出。对于乡土地名的古今比对考证,特别困难。赵先生生长川南,谙熟乡邦,通过长年大量的田野、社会调查,系统,准确地考证出宋代泸州及其周边地区乡土地名对应于现在的什么地方,不仅难能可贵,更是相当庆幸。
二,历代传统的文献校注著作,大多只是引经注典,引用文献的文字进行校注。这与中国历史上从图经时代逐渐走向文字时代有关。近年,随着图像史学的兴起,在历史研究中,渐有学人开始使用图像资料。我们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和《重庆历史地图集》,就尝试运用一种“三分式”的表达形式,展现研究成果。而在传统的古籍校注中,这种范式则尚未得到普遍使用。赵永康先生年事虽高,学术研究与时俱进。早在他的《川江地理略》书中,就已大量引用地图、图像资料,印证历史。这种以图证史的方法,在《永乐大典补图注》里,得到了更多更好的运用。拓宽了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途径和文本形式,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由于史料缺乏,绘出的宋代巴蜀地区的城市地图极其不易。比如《成都城坊古迹考》,虽然绘出了宋代成都城图,但至为简略,我们的《重庆历史地图集》,则未能单独绘出宋代巴县城图。降及地级城市和区县,这样的地图,更是至今无有。《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科学绘制了宋代泸州城池,街坊里巷之图,城墙、城门和各种功能建筑,街道坊巷,定位准确,一目了然。功莫大焉。
赵永康先生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识途老马身犹健,不用扬鞭自奋蹄。”潜心学术,笔耕不停,叠有新著问世。后学叹服不已,以此为序,深表敬意。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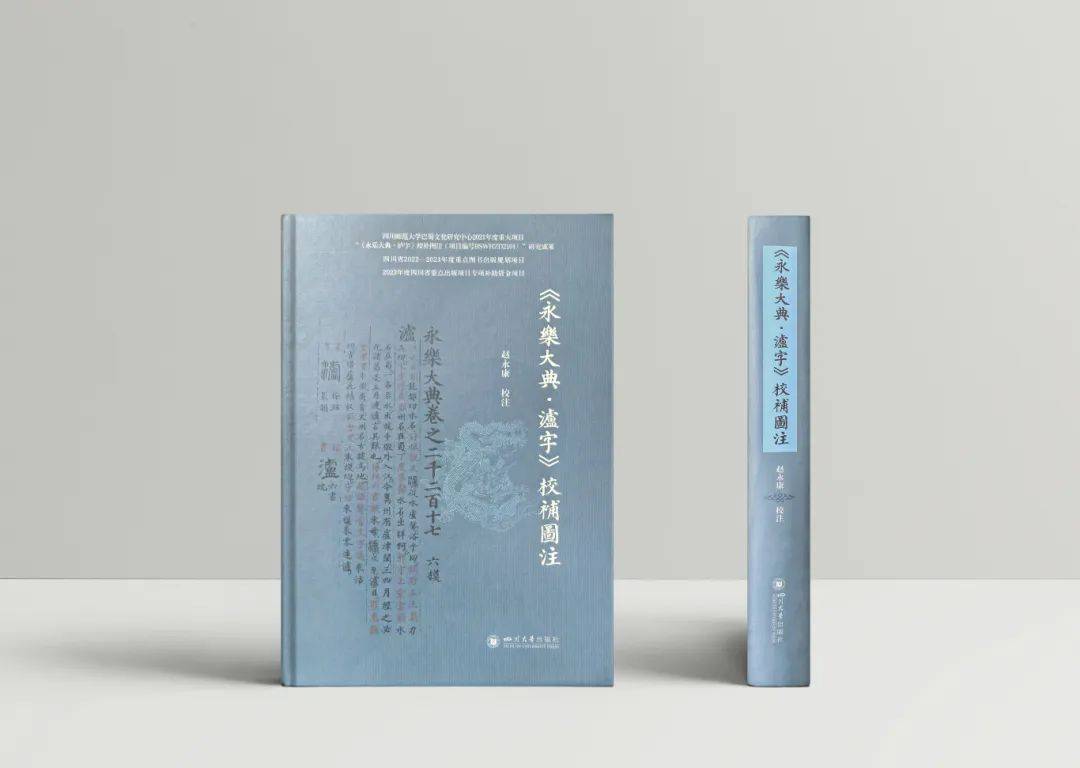
包伟民先生序
2017年6月13-14日,我应邀到四川泸州,参加由当地政协组织召开的“宋代泸州历史文化与宋城文化的保护利用研究”开题会。在参观了闻名已久的神臂城以及精致的南宋墓葬石刻后,我们一群外来和尚,对于怎样开展关于泸州两宋时期历史问题瞎出主意。我因为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曾经有所利用,对于被保存在《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南宋名志《江阳谱》印象深刻,遂在会议上提出建议,认为整理以《江阳谱》为代表的地方文献值得重视。不想五年后,泸州文史耆宿赵永康先生,真的将他一部五十四万言的《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发送到了我的电子邮箱,命我写序。
地方文献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学界的常识。我们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常常悬浮于半空,围着中央政令打转,难以深入到历史社会的基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相比于社会上层与中央层级,涉及基层社会的历史资料太过缺乏。地方文献常常能够提供比其它记载更多的基层历史信息,因此受到学人们的重视。在文书档案资料极少保存下来两宋时期,方志就是最为重要的地方文献了。
现存两宋方志,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地区。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几乎将宋元时期地方志收罗无遗,其中收录的三十一种宋代地方志,除了《长安志》《雍录》等少数几种属于西北地区外,总共有二十五种出于江浙地区,另有一部重要的《淳熙三山志》出于福建地区,不多的几种元代地方志的地理分布也是这种情况,出于四川地区者则完全付诸缺如。多年前曾有学者利用《永乐大典》残本,辑录其中收录的地方史志遗文,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宋代文本,例如南宋连州的《湟川志》即是。但其中文本体量最大的当数《江阳谱》。尽管已非全帙,仅有模韵泸字的第二二一七、二二一八两卷,收录了明人利用旧志修成的十三卷泸州地志中很少的一部分,其中以南宋曹叔远所纂《江阳谱》和后来的《江阳续谱》等宋元地志遗文为主,所以学界大多习惯性地以《江阳谱》来概指这两卷所收录的泸州地志资料。其价值之高,几乎成为了学人们讨论宋代相关议题时不可或缺的资料。例如其目录所指示的,无论是州县建置、城池修筑、坊巷布局、户籍人口,还是赋役征发,都是如此。特别是关于南宋时期的乡都体系与专门的治安、消防等组织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存世最为详细的地方性记载。对于那个时期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中,作为通行条贯颁布的诏旨法令,在其具体落实过程中常常会形成五花八门的地方性版本,反映出从中央到地方不同行政层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诏旨法令与各地环境之间的磨合。《江阳谱》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例证。例如,北宋初年整顿乡里体系,在每个乡之下置里与耆,里设户长以主催科,征赋役,耆设耆长主治安,稽盗贼,一般称之为乡里制。地方实际执行,则常常调用治安力量以协助催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由治安组织越俎代庖,取代户长的现象。《江阳谱》的一则记载就相当典型,多为学人们所引用:
今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
到宋代,乡与里虽然已不再是基层管理组织,但税籍依乡而定,里则作为地名体系而存在,因此当时的人们讲到籍贯,仍“书乡里名”。官府税籍分隶耆下,即将征赋催税工作交给各耆,而不像大多数地区那样由户长、以及后来的保甲组织来承担,则是泸州特别的做法。这就是制度“地方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所谓普遍性,其实只有通过对各地众多个例的归纳与抽象,才能得出。我们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认识,也只有在这样的归纳与抽象中,才能得到深入。这就是地方文献核心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此外,《江阳谱》对宋代泸州城区布局的详细记述,尤有价值。从唐到宋,泸州城区几度改建,城池与街坊里巷前后变更不少,但城区中心一直位于长江与沱江交汇的半岛形地区,以取其交通与防御之便利。由于地形“高下不齐,不便于建市”,不得不与长江江岸平行,从南向北建为长街,东端则向西延伸,建为另一条主长街。这种十字形街道布局,与当时平原地区城市多数作方正形布局大相异趣。《江阳谱》对南宋时期泸州城区布局、坊巷关系、市场形制等等情形,都作了详细的记述,本人几年前讨论宋代城市史的几篇小文,受其惠多矣。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今人了解泸州的城规历史、以便在新城区建设中尽可能保存历史旧貌,推陈出新,提供了方便。
例如讨论宋代泸州的羁縻州蓝州(蔺州)的城址,经过文献比勘与实地考察,指出应该在地理富庶的柏雅妥洪,而不会在地势偏僻的唐朝坝,并据此得出结论,“所谓蔺州、蓝州、能州、归徕州,其实同为一地,即今古蔺、叙永一带,治于古蔺县县城。《宋史》所谓‘泸州羁縻州十八’,实际只有一十七个”。这样的考证,我看是可以成立的。又如校勘江安县的耆、都之名,其中有“山南耆”,但其后文又作“生南耆”,二者以何为正?赵先生指出:“今按该耆地望,当时盖不承租赋的‘生夷’之地,且无大山隔断南北,用改作‘生南耆’。”如果不是依仗谙习地方的丰富知识,这样的判断也无法得出。
同样地,对泸州城区新旧地名的对勘研究,外人更难以措手,非乡耆如赵先生者,对城区街巷地理烂熟于胸者不能及此。
正如赵先生所指出的:“前代史家据书考地,而文献不足征引,又乏考察实践,用多因缘旧说,不能无疑。”诚者斯言。
赵永康先生是学术前辈,虽然应其命作“序”,实际只是借先读之缘,简单说几句自己拜读后的心得,以求教于赵先生与读者诸君。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王川先生序
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泸州,是坐落在长、沱两江交汇处的川南古城。这座长江上游的重要口岸城市,古称“江阳”,因江而繁盛,与重庆同为“老四川”最重要的港埠。特殊的地理位置,人类的早期开发,农贸的发达,便利的交通,繁盛的人口,使泸州很早就成为西南地区的战略重镇,明代更成为与成都、重庆鼎立而三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于今可谓川滇黔渝“四省(市)通衢”。泸州开发史起源甚早,江阳县的建置,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东汉升格为郡,南朝梁代改置为泸州,地名沿用至今。
自古以来,众多名家为泸州编纂过方志,其中南宋曹叔远就编有《江阳谱》。受朝代更迭影响,这些古老的方志,大多已经佚失于战火之中,幸而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辑录了《江阳谱》《江阳续谱》等宋元地志遗文,以及汉晋以来《太康地志》《祥符州县图经》《皇朝郡国志》《元一统志》等散佚旧籍,以及《华阳国志》《水经注》《元和天下郡县图志》等多种珍稀典籍中有关泸州部分,编为《永乐大典》“模韵泸字” 十三卷,极具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永乐大典》历经时代风雨,尤其是遭遇八国联军侵华战乱影响,散佚甚多。其“模韵泸字”十三卷,仅存第二二一七、二二一八两卷。清代光绪末年,翰林院编修、文献学者缪荃荪,从内府将此二卷抄出,题作《泸州图经》。民国二十五年,成都美学林排印出版发行,改题为《永乐泸州志》,成为民国时期刊印的四川最为重要的地方志之一,亦是目前可见的西南地区重要的方志文献。
二
《永乐大典》模韵泸字残卷,在几百年的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篇章紊乱、错字漏字、史实误差。有鉴于此,知名文史学者、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赵永康先生,慨然发愿,进行艰难的文献整理工作。以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的《永乐大典》为底本,与1936年美学林排印本《永乐泸州志》互校,而以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为归依,对现存《永乐大典》模韵泸字两卷进行校正、勘误、补充。考献征文,日新其业,历时八年,撰成了《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之书。
这部学术著作,在将原文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按照国家标准科学标点断句的同时,结合当代学人研究最新成果,以“补注”形式,校正原书记载的失误,补充新的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金石文物,并对原书若干问题提出了商榷。全书分为图、建置沿革、郡名、分野、至到、城池、坊巷街道、乡都、桥、渡、园、风俗形胜、户口、田粮、土产、土贡、山川、宫室十八章,另附明成祖文皇帝御制永乐大典序、永乐大典凡例、永乐大典泸州遗文和历代泸州建置沿革大要四个附录。引录前代典籍一百八十二种,成文五十四万有余言,补入古今地图、图画、照片九十八幅,题作“校补图注”。
本书在历史文献整理领域的最大特色,在于“校补”及“图注”。所谓“校补”,就是历史文献学所谓的“校勘”和“补注”。前者系指凭借专业理论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排比校勘,综合考定,以科学的态度校正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篇章紊乱、字句错讹、史实误差,恢复典籍文本的原貌。后者则是对原书内容进行注释、补充,发明和驳正。二者皆为文献学的传统方法。《永乐大典》模韵泸字作为记录泸州的重要典籍,由于历史条件制约,不无错漏,永康先生对于原书的脱漏和错字,有的根据历史典籍予以校正、补足,例原书记录泸州“命赵金还故治”一条,原文因“金”与“全”字形相近,误“金”为“全”。根据《元史·世祖纪二》予以订正;又如 “建置沿革”章记载“晋于此立江阳郡”,根据《宋书》补足遗漏的“东”字。除了这种基础的查勘补漏,永康先生还参考前贤郦道元注《水经》和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方法,扩大了“补”的范围,对原著未曾涉及但又值得补充的事物,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和地理测绘、考古等多种现代学科手段,进行了更深层次、更大幅度的补充和订正。例如在第四章“分野”中,批判“分野”方法不科学,改而采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测古今泸州若干处所的地理坐标,经纬度精确到秒;在第六章“城池”中,则根据原书记载,结合当今地理实际,深入探求考证,进而运用现代绘图方法,绘出宋代泸州城池及其街坊里巷之图,直观再现了宋代泸州城市的原貌。这种“校补”方法的科学运用,是为本书的重大特色之一。
“图经”,又称图志、图记。指附有图画、地图的书籍或地理志。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记述地方情况,古有东汉《巴郡图经》,后有任乃强《西康图经》诸名著。永康先生师其要旨,补入古今地图、图画、照片九十八幅,并且给予必要的阐释。图文并茂,一目了然。
《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的另一大特色是“考证”。永康教授以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与徐中舒先生“多重证据法”为圭臬,通过进行田野、社会、文物调查,结合历史文献,对于川南黔北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勉力考证。例如在“郡名”章中,综合历代包括常璩、辛怡显、李、杨升庵以及任乃强等诸多学人的意见,考证诸葛亮南征并未经过泸州,从而得出其“五月渡泸”的渡口不可能在泸州的结论;在第十七章“山川”中,则对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开展考证,认定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路线,不仅有任乃强教授生前所说“从蜀西南经滇缅去印度,有一条原始的商道。”还有自合江沿着汉代唐蒙通夜郎的足迹,溯赤水河进入贵州,最后从广州出海的另一条商路。这是因为从成都经岷江到宜宾入长江,过泸州到合江转赤水河进入贵州,转牂牁江(即北盘江),再转红水河、西江,可以直到广州。这条线路不仅有《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予以记载,还有赵永康教授本人在合江所发现的唐代“胡僧”造像以及其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棺考古证据予以佐证。进而提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是多线路、网络状,代有变化和发展的商路的新说。
除了考证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问题,赵永康教授对于泸州的土产方物,也进行了翔实的考证。泸州自古盛产荔枝,宋代以来,就有唐代杨贵妃所食荔枝系泸州所出产的传说。本书从保鲜技术和运输条件科学的角度出发,对该说予以反驳,认为在没有真空密封冰冻技术的唐代,荔枝保鲜,最多也就只能是裁截竹筒,一端留节,把荔枝放在里面,口部塞上绿色植物,再蒙上油纸扎紧,糊上泥土进行密封,避免太阳的直接照射,让筒内温度稍低于筒外的气温而已。这种竹筒保鲜法,在荔枝成熟的夏季,即使静置在太阳光直接照射不到的阴凉处所,三四天过去,也会味变不堪食用。无法从泸州将荔枝七天七夜送到长安。提出杨贵妃所食泸戎荔枝,只能是《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志》记载的通过渍制加工的“荔枝煎”。这一分析,令人信服。
三
历史文献的整理,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专业文化知识,通过古代汉语、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校勘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运用,方能校正误、理顺序、定去留。《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在传承中国传统文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同时,不是单纯“以书考地”,袖手寂坐书斋。而是尽到著者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发展的责任,知古鉴今,经世致用。
例如在考述北宋时期修建泸州土城时,专门加写 “编者按”,总结泸州筑城成功的经验在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中央与地方政府齐心协力,就可以将城防建设好;在记述“熙春园”时特别强调,在宋代即使是官家的花园,春暖花开时节,也要向民众免费开放。这与当前时代让全体国人享受祖国灿烂文化的文化“获得感”异曲同工。这样的论述,在全书还散见于多处。
通过校补图注《永乐大典泸字》,著者达到了通过参校诸多文献完成一部善本泸州方志文献的初心,增加了读者对于历史上泸州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便于了解川南尤其是泸州地区的历史变化,并且可以举一反三,科学认识整个川滇黔渝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经济、人文地理发展状况,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战略决策,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学术理论支撑。
壬寅年七月二十九日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蓝 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
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宋史学会会长)
王 川(四川旅游学院校长,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