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张中信:比较诗学的跨时代研究——以旧体诗集《邀月集》为例‖李桂玉
张中信:比较诗学的跨时代研究
以旧体诗集《邀月集》为例
李桂玉
张中信是当代旧体诗的拓荒者,在三十余年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作出一些好作品,描绘了人生的绚丽多彩,折射出时代的生活百态。其中,《邀月集》便是他旧体诗创作的一部力作,其深刻性、创造性在诗歌界得到广泛赞誉和研究热情,从历时三十多年的“新古体诗”到现代“格律体”的创作发展,他不仅实现了诗风的完美蜕变,也经历了时代对个人思想的重大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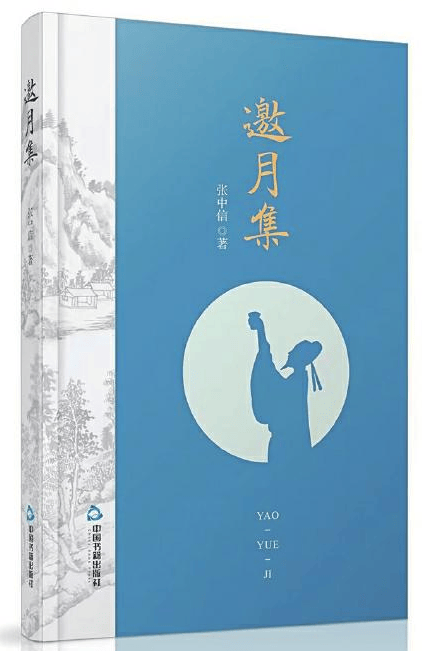
图源:《消费质量报》
张中信从17岁开始在大巴山深处板板桥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一边从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边开始文学创作。《唐诗三百首》便是他的教材,李白便是他的老师,同时还受到过当代诗坛叶嘉莹、吴丈蜀等诗词名家诸多影响。龚自珍曰:“儒、仙、侠实,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这些不同的思想碰撞,最终让这位大巴山之子从此投身诗海,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并在天命之年痛下决心,“卷土重来”“勒马回缰习格律”,最终实现诗词创作的华丽转身。
一、张中信旧体诗创作所受的主要“影响”
(一)“新古体诗”的影响
首先是传统与创新的融合。张中信早年的“新古体诗”创作之路,主要受当代大诗人贺敬之新古体诗的影响,新古体诗虽然不严格讲究音韵平仄,但刚健有力的风格,却让人耳目一新。贺老一生追求诗歌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而摒弃古体诗的音韵格律,为自己量身设计了“一匡天下”“立抵卿相”的传奇路径,并豪言“功成而不居”。这种诗词创作的开放思想,让张中信大受鼓舞,并为之付出艰辛实践,创作出大量“新古体诗”。三十年后,这种旧体诗歌创作“路径”,却让他卷入争议的漩涡,赞誉者固然有之,但不少批评者认为,“新古体诗”并不符合传统近体诗的创作范式,已不再被诗坛主流所接纳。这些争议,让他的古体诗创作一度陷入迷茫和困顿。
尽管不符合传统近体诗的创作范式,但张中信的新古体诗作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一朵“浪花”,他成功地将传统诗歌形式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风格,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孟子曾说“知人论世”,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从张中信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时代背景上研究,《邀月集》首先是“传统”与“创新”的结合。张中信的现代“格律诗”在形式上保留了古典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但内容上却又大胆创新。如《过都江堰》第四卷成都书第125页:“一堰润天府,二王称蜀主。去来皆浮云,玉垒知今古。”第一句直接点明“润”字形象表达都江堰水利工程对四川平原的灌溉与养育,突出文化精神重要性。第二句“二王”是都江堰建造者,后人称为“蜀主”体现人们对他们的崇敬和感激。第三句暗示人生的短暂与无常,无论是功名利禄还是历史的辉煌,这是社会的现实。最后一句“玉垒”指都江堰附近的玉垒山,这是人们现代的繁华与财富。既尊重古典诗歌的美学传统,又突破传统诗歌的题材限制,将现代生活、文化精神、社会现实等主题融入其中,使诗歌既有古典的韵味,又具有现代的气息。
其次是“理想”与“现实”的表达。张中信的诗歌创作深受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以意逆志”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理想的热情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思考。以深情的笔触表达了对革命圣地的怀念和对革命精神的颂扬,展现了诗人对革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情感共鸣。
第三是语言“艺术性”的追求。张中信的现代“格律诗”诗在语言上追求简洁、凝练,同时又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他很懂得古今字、通俗字、字形与字形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方式,并注意用典、礼称等文化习俗,在此基础上他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修辞手法,如对仗、排比、比喻等,使诗歌在形式上保持了古典的美感,但在语言表达上辞藻和词采充分展示了自己语言艺术的才华和风格,同时又与近现代人的情感和思想更贴切。古诗词从美学风格上看,清新自然的素朴美与饱满丰富的繁复美都是我们欣赏的。如《父母书》第三卷还乡记第117页,写思念父母的音容之美,可谓是极尽描绘之相思:“音容宛在梦追随,千里相思何日归?辗转每怀嘘暖语,飘零犹忆寄寒衣。”说到朴素之美,这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种不加修饰的简洁洗练的语言审美形态,通过白描简洁手段以达到形象传神、含蓄隽永的创作目的。这里“音容宛在梦追随,飘零犹忆寄寒衣服”,这两句不求浓艳绚烂、丰瞻精细,而求淡雅、简练朴素之美。单从中国传统审美趣味来考察,张中信创作中语言艺术境界中的朴素之美、自然之美,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如王维和孟浩然并称的“王孟”,这种功夫被很多文人赞誉为“真文采”,可谓是“语淡而味终不薄。”
(二)传统文化的影响
张中信生长的板板桥,地处大巴山深处的米仓古道(汉壁道)要津,是巴文明的基因库,是秦汉文明的走廊。秦、蜀、楚文化在此融合,儒、道、释思想在此交汇,各种传统习俗在此碰撞,形成了多元融合的特点。“飒飒清风作胜游,烟波摇落一江秋。凭高欲对天公语,谁可千年主沉浮?”(第2卷巴中诗第84页)此诗即可见证张中信儒、道思想的融合,道教神仙思想,赋予了他奔放飘逸的个性;儒家家国理念,又给予了他心系天下的胸怀。他酷好自由、“志不拘检”的个性,投射到诗中便形成了张中信天马行空、神与物游的豪放风格,以及“才逸气高”“格高旨远”的飘逸美学。“群山赴万壑,曲径入翠微。我来弄鸣琴,抱得溪月归。”(第二卷巴中诗第92页)这种率然而成的诗风,不仅体现出孔儒心智充盈、乐以忘忧的境界,同时也暗合道家任运适性、不施人工的思想。
(三)老区精神传承的影响
张中信17岁出道,从乡村一路拼搏到都市,三十多年不断努力,旧体诗创作从未间断。“一言兴诗、建立奇志”的思想影响了张中信“一代诗者垂拂拭”“直上青云生羽翼”的人生设计。这种一心在旧体诗上不断求索的思想,充满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一旦高远的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又会在张中信的心中激起巨大的感情波涛。追求奇功的梦想和理想破灭后的困境构成了张中信诗歌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巴山儿子,革命老区的历史浇灌,红军精神的不竭传承,对张中信的个人成长影响深远,这种影响融入他的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张中信诗歌的奇情壮采,所谓“想落意外,法老而奇”“无所不包,奇之又奇”。
(四)浪漫主义情怀的影响
《蜀道难》词意曲折,“乱处、断处、诞处惧从《离骚》来,骚体式也受楚辞影响,以至有人说‘古今诗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张中信《望岳阳楼过洞庭湖》第5卷第173页)词意曲折,楚梦、楚云、乾坤,“最有楚人风”,几“与骚无异”。他既继承了“风雅精神”,又深受李白、王维的影响。诗歌中的气势磅礴、想象奇伟与李白的影响一脉相承。比如:“放舟千棹起,呼酒一垆开。邀月枕溪上,长卿入梦来。”(第四卷成都书第124页)“摩天壁立势何雄?云外一山秋气浓。百转千回仍向上,我身飞过最高峰。”(第四卷成都书第142页)他的诗如同唐代铜镜上的鸾鸟,历经千年锈蚀反而显神秘光华。那些缠绕的意象、加密的情感、破碎的时空,最终在读者的阐释中完成意义的再生,这正是张中信诗歌包含张力的生命力所在。
二、张中信旧体诗主要的艺术特色
(一)开合的气声力雄
张中信的旧体诗读来让人感觉气势奔放,以气度人,而且这种气势一贯到底,一气呵成,惊风泣雨。他的诗歌佳处难以泣得之文章,气势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强烈的自信和傲视,以及独立的人格力量。自古以来,气势贯通乃文章的血脉,文章气盛则有力气,方可具有撼人心气魄的力量。《登庐山》“附葛试登攀,莺飞水郭间。欲追太白迹,寻梦上庐山。”(第五卷四海风第165页)此处“攀”“追”“太白迹”,彰显了张中信气盛言宜的主张,他以水为喻,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伏,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郁孤台》:“云水无声送归棹,江山有郁上孤台。凭高顿觉星河近,极目豁然天地开。”(第五卷四海风第181页)云水之急也不厚,则其覆星河载尔逍遥游。这些诗气势充沛,艺术感染力非常巨大,如天风海涛。作品的气势正如庄子《逍遥游》鲲鹏运行九万里云涛之上,传达出巨大的力量感。张中信习惯选用壮大的意象,如《鹳雀楼》第五卷四海风第169页“落日千山外,长河九曲流。我来无一字,也上鹳雀楼”。情感基调经常在高位运行,“千山”是基调,情感变化幅度大开大合,转身一个“九曲流”,最后一句“也上”二字,则是顶点和低速之间落差巨大,制造出强烈的冲击力。又如《大小孤山》“江海望中舒,恋峰水上呼。扁舟横浩渺,大小亦称孤。”(第五卷四海风第161页)“江海”和“扁舟”形成了顶点和低速落差,海是浩大的,扁舟是渺小的,形成了回旋之美,自然浩大,万物渺小之镜像。再如《桃花源》“梦境越千年,武陵犹问津。桃源寻旧迹,谁是打鱼人?”(第五卷四海风第171页)一朝开光耀了千年,后世仰未照好大陆。梦境与现实不断交织,中年后的我与高凡伟岸的古人们还有一些差距,我和桃花源的那个渔夫一样,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桃花源”,这是千古之理想,也是人人之追求,我会是那个发现理想世界的“打渔人”吗?古人和现在的我形成了强烈的空间冲击力,读者脑海一下子穿越到了千年,情感张力大开大合,落点在“谁是”,这个“谁”也可以暗指任何人。
(二)奔放的审美情感
从审美情感的内容上看,张中信的旧体诗都是个人鸿鹄之志的歌唱,也有理想破灭后对失意情绪的倾泻,有长风万里的信念宣言。
从审美情感的强度来看,张中信诗作的情感豪迈奔放,如同惊涛拍岸,火山迸发,具有强大的爆发力。他常利用强对比造成震撼性的效果,“悠悠湘楚梦,风雨岳阳楼,鸥戏一湖水。浪打百年舟,天远空怀策,山深独抱忧。”(第五卷四海风第173页)悠远的湘楚文化让我想念,心情无限叹息,看着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常在岳阳楼叹息理想,风雨千年的岳阳楼,历经时代变迁与人生坎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人生之困顿,让张中信对时代的抱负有了更深切的思考。最后两句则表达了对理想难以实现的无奈,在孤独中坚守责任与信念的情怀。张中信喜极端变化的情感如其苦,俱哀俱痛写“杜洒乾坤泪”,极端忧思抒发写“辗转不休天命年”,哀伤解愁写“此日老街离恨多”,超脱世俗写“仙池洗尘容”,打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颠覆了传统的平衡美学,读来令人心折。
从情感变化的魅力来看,张中的诗歌“章法继承,变化无端”,遵循的是意脉逻辑,如李白之文同妙,所谓意接辞不接,往往先写壮志受挫的巨大失意,最后再写低谷时重燃信念的上扬。如《乙亥杂诗》“苍茫何处问风流?清梦悠悠恨白头。”(第六卷浪子吟第203页)这两句暗喻现实的混沌,理想的虚无,理想的境界已湮没于时代洪流中,无人问答,无处可寻找。“恨白头”则将抽象的时光流逝具象化为白发的生长,突显理想未竟而衰老已至的悲凉。“平生最信真与善,世事遑论放与收。”这两句“真和善”是诗人一生追求的核心价值,体现了一种对道德与人格的崇高追求。这种信念超越了世俗的功利与得失,成为诗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放与收”代表了对人生起伏的淡然态度。诗人认为,世间的得失成败不过是过眼云烟,无需过分执着,应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真和善”与“放与收”形成对比,前者是内在的信念,后者是外在的态度,二者变化无端,但意脉逻辑相互呼应,共同构成诗人的人生哲学。前句强调“信”,后句强调“遑论”,一正一反,增强了诗句的张力,表达了人生信念的坚守。
张中信的情感是发散的,还常常营造一种带有奇幻色彩的壮美。如《庚子感怀》之四“携酒归来每倚楼,晴霞处处见清秋。风回汀沙半江碧,雨打珠帘一枕休。沧海无声知得失,云山有迹问沉浮。闲看鸥鹭飘飘起,独向五湖寻钓舟。”(第六卷浪子吟第214页)第一句“携酒归来每倚楼”,借酒登高来消愁;第二句“晴霞处处见清秋”,晴朗的霞光遍布,点明了季节清秋。清秋凉爽、明静,在这里有隐含萧瑟之意;第三句“风回汀沙半江壁”,风和水的变化隐喻指时间的流逝,诗人心情的波动;第四句“雨打珠帘一枕休”,雨点打在珠帘上,诗人独自一枕休息,雨和珠帘营造出宁静孤寂的氛围,结合前面的酒和楼,这里有避世的心态。接下来是颈联,“沧海无声知得失,云山有迹问沉浮。”沧海无声,沉默着,是诗人对得失的淡泊。但云山有迹,山的轮廓若隐若现,仿佛是在询问世事的沉浮。最后两句“闲看鸥鹭飘飘起,独向五湖寻钓舟。”闲看鸥鹭飞翔,独自去五湖寻找钓船。鸥鹭是自由的化身,钓舟是诗人对自由向往、生活归隐的心境。诗中酒、楼、晴霞、风、雨、沧海、云山、鸥鹭、钓舟这些主体完全屈服了客体压倒性的力量,充满“奇险之旅”“超然物外”的意境。这首诗承袭唐代山水田园诗传统,又融入宋诗的理趣,兼具意象之美和哲理之美。结构上前两联写景叙事,后两联抒情言志,起承转合自然,语言上,巧用色彩对比(碧江、晴霞)、动静结合(风回、雨打),营造出清旷深远的色彩之美,意境之幻。
(三)想象的奇险艺术
想象丰富奇特,大量运用历史典故传奇元素,营造出了迷蒙堂皇的飘逸美。第六卷浪子吟第217页《辛丑秋怀》:“每忆家山伤寂寞,梦中谁在说南柯?”“南柯”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典故人物,出自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后来被广泛运用,成为“南柯一梦”,形容虚幻的梦境了了一空的经历。“听雨三更惊短笛,弹冠十载对长歌”,“三更”与“十载”形成时间上的对比,前者象征短暂的瞬间,后者象征漫长的岁月;“听雨”与“弹冠”分别象征沉思与行动,暗示诗人在经历孤独与反思后,重新针对面对人生。而“弹冠”和“长恨歌”又表现了一种重新开始与抒发情怀的决心,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写南柯一梦的传说想象与现实想象之间变化多端而又衔接无痕。想象奇特,打破了创作传统和接受期待。如“邀酒狂呼太白杯,笑对青山独徘徊。”“卅年奔走镜中雪,十里啁啾林下莺”。变化不可聚集,变幻、恍惚通篇其险。
三、张中信旧体诗展示的壮美意象
首先,诗歌创作中的一批批壮大的审美意向。诗人的意象思维是非常突出的,诗中头脑所形成的自然和生活图景又与表现的情志相融一致。“意象”这个概念是中国文学理论的贡献,具有象征意蕴的文学形象,特点是富于灵感性、知觉性、形象性、跳跃性、顿悟性和创造性。张中信的诗中最具有意象的字有云、月、雁、舟、酒、归、寻、烟波等。在诗人的酒、月、舟、烟波意象系统中,酒最狂肆,舟最孤单,月最灵妙,烟波最忧愁。他以“人月相得”的诗学意兴,借那轮高悬苍穹的明镜,洞彻肺腑地进入天地对读、自然与人情互释、内心与外界沟通的幻想创造,从而为后现代诗人开发了一个韵味清逸而美妙绝伦的灵感源泉。
其次,诗中主导意象和次要意象搭配。如《诺水棹歌》之四第一卷诺水赞第31页,在“白云”意象的统领下,诗人还写了大荒、一舟、渔笛、海楼、清流,乃至不眠的游子在外漂泊的意象,在这一切景物人事都笼罩一层银白色的面纱,从而营造出清幽深远、海市蜃楼的朦胧之美,充满祥和意境。多个意象并置在一起又迭印另一个意象,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以达到增强意象表象力,给读者带来新异审美感受的效果。又如《诺水棹歌》之七第一卷诺水赞第34页:“诺水千家雨,巴山几处花?江流飞玉带,渔唱乱昏鸦。寻迹迎归客,悬灯照钓槎。峣峣知何在?一棹月无赊。”这首诗中,千家雨、几处花,烟雨与山花意境充满水墨画的湿润感,又暗含繁华易逝的叹息。江流和玉带动态中见壮美,“玉带”也暗含江流如帝王腰带,赋予崇高感。渔歌和黄昏归巢的鸦声交织,“乱”字既写声音的混杂,又暗示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冲突,凸显暮色苍茫中的生机和躁动,视觉和听觉相结合,动静相生,画面层次丰富。颈联部分寻迹和钓槎分别暗指渔人归舟和希望。尾联部分峣峣和一棹,暗指人生理想归宿和目标,小舟漂泊不定、时光催迫,月不舍,唯有孤舟随月影不停漂泊,强化孤单感,以山高难寻,孤舟逐月的意象收尾,表达人生归宿的终极追问和漂泊宿命的无奈。诗中以巴蜀山水为载体,通过雨、江、渔、月等意象,交织出自然之美与人生之渺小,核心表达“追寻与漂泊”的永恒矛盾。
为表达壮大的审美情感,张中信在诗中还多用夸张排比的手法。如《辛丑愁怀》第六卷浪子吟之六第223页:“几度沉沦犹进取,一身抱负难迎逢”。将人生诗意写到“绝望”境地。张中信采用夸张式,更多使用的是夸大,便于塑造壮大的审美意象。“西与东,独悲风,几番劫,一枕空”,这一组的意象,象征诗人人生的梦幻感、悲痛感、哀怨感和迷惘感。
还有,恣意妄为的意向流转。张中信喜欢用白、青、红、霞光等明丽色调,对明月这样的秀敏体青睐有加,而对伟岸的物象不感兴趣,把诗歌的语言纯净自然,明丽爽朗,清新流转。
诗人还善于把多个意象并列,将若干个意象平铺排列,意义上互为生发,共同营造诗歌含蓄隽永的意境。如“前路何曾见缈迷?断鸿声声独南飞。”(第六卷浪子吟第215页)“雁归危栈后,猿啸落红前。”(第一卷诺水赞第11页)而在长篇古风《空山月》中第一卷诺水赞第55页,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
卅年栖栖访旧踪,空山晚在梦魂中。
青峦迤逦腾洁渺,碧水潆洄盘空濛。
太白烁烁凌霄汉,高鸟飞飞出葱茏。
夜静山空涵苍翠,清露无声湿梧桐。
明月青天本高洁,空山悠悠喜相逢。
人生浮沉故旧疏,世事无常古今同。
空山明月两相望,玉盘清辉自浑融。
把酒向天歌声彻,我来邀月醉颜红。
人生如月有盈亏,月月轮回亦有终。
岁月悠悠逐流逝,明月灿灿笑清风。
在这首诗中,诗人将意象进行了扩散,以诗人意识中的情感流动为线索,不断涌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意象,更好地表达诗人丰富细腻的心灵世界。诗中很多自然意象,如空山、青峦、碧水、明月,这些通常用来表达对自然的向往,在追求过程中的孤寂,感慨时间的流逝,寻求超脱的心境反复出现。诗中反复出现的“空山”和“明月”,这是诗人对清净和永恒的追求,与“人生浮沉”“世事无常”形成了强烈对比。“把酒向天歌声彻,我来邀月醉颜红。”是豪迈的心境,是借酒消愁的情感表达。第一句“卅年栖栖”暗指半生奔波劳碌。“空山晚在梦魂中”暮色中的空山如梦如幻,象征追寻的虚妄与记忆的缥缈。第二句“青峦迤逦腾洁渺,碧水潆洄盘空濛”。青翠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绕(“浩渺”);碧绿江水迂回流转,雾气弥漫(“空濛”)。意象又再次得到体现,以山水之“动”(腾、盘)反衬心境的“静”,自然永恒与人生短暂形成对比,这是情感的自然流动。第三句“太白烁烁凌霄汉,高鸟飞飞出葱茏”。“太白”隐喻李白式的超逸,光芒璀璨直冲云霄;“高鸟”冲破葱茏山林,象征对世俗束缚的挣脱,借星月与飞鸟,暗示对精神自由的渴望。第四句“夜静山空涵苍翠,清露无声湿梧桐”。夜静山空,苍翠浸染天地,清露悄然沾湿了梧桐。这里意象展现在以“无声”凸显空寂,露湿梧桐暗示了时光流逝的细微痕迹。第五句“明月青天本高洁,空山悠悠喜相逢”。意象推高,明月青天是高洁永恒的象征,与空山“相逢”,体现人与自然的精神共鸣。这里从苍凉转向超然,为后文哲理升华作出铺垫。第六句“人生浮沉故旧疏,世事无常古今同”。直言人生起伏、故交零落,世事无常是古今共通的规律。由景入理,点明“变与不变”的永恒命题。第七句“空山明月两相望,玉盘清辉自浑融”。空山与明月对视,清光浑然一体,暗喻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处升华了自然成为超脱的象征,消解人世纷扰。第八句“把酒向天歌声彻,我来邀月醉颜红”。对月饮酒唱歌,醉态中显豪情,化用李白“举杯邀明月”的孤傲与放达。借酒与月,情感宣泄对现实的疏离与对自由的追求。第九句“人生如月有盈亏,月月轮回亦有终”。以月之盈亏喻人生起伏,但明月永恒轮回,而人生终有时。末句“岁月悠悠逐流逝,明月灿灿笑清风”。将自然拟人化,诉说时间无情与生命有限的释然,在自然永恒中寻得对人生短暂的慰藉。
整首诗中意象群构建是平列的,意境互发,“空山”生“青峦碧水”,“空山”又生“明月”,“明月”又照“空山”,三种事物共同构成超脱尘世的理想空间。而在情感时空的张力体现在“时间”卅年奔波“短暂”和“明月轮回”永恒;“空间”人世浮沉,“局促”和“空山苍茫”,这种“无限”强化人生与自然的对比。语言风格上充分融合了李白的豪放浪漫,“把酒邀月”又与王维的空灵“清露湿梧桐”,形成清逸与沉郁交织的诗境。此首诗以“访旧踪”起笔,以“笑清风”收尾,通过空山明月的一系列意象群,完成了一场从“人世苍凉”到“天地释然”的精神漫游。诗中既有对人生短暂的悲悯,又有在自然永恒中寻得安宁的豁达,堪称现代语境下对古典“山水悟道”传统的延续与重构。
张中信旧体诗集《邀月集》在古风、绝句、律诗等创作上有感于大雅不作、绮丽成风,抒发了志在删述的理想。他继承了李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作大量的五言七言律诗。用其本意,从历史中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胡震亨《唐音癸签》),从主题上没有完全摆脱古体诗的规约,仍大体符合了现代诗歌格律的赋体等传统,代以抒情和议论,为现代诗歌注入了强大生命力,以浪漫主义的笔法来写时事,充满了奇情壮采,读起来“一唱都护歌,心催泪如雨。”同时,张中信在拟古中展示了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表达的是诗人的自我情怀。作品中展示了诗人发兴无端、想落天外、气势如虹、豪迈奔放的艺术个性。将人生之困惑、困境,拟古以申己意,处处有“我”,展示出强烈的艺术个性。
随着《邀月集》的出版,张中信完成了从“新古体诗”向现代“格律诗”的华丽转型,并且创造性地推动了五七言为主的杂言体诗的创作和创新。我们看到,他在诗中贯注人生的理想与失意、挫折与坚持等,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色彩,狂放豪壮;“一气呵成,最得歌行之体”,还善于从高处俯视人间疾苦,反衬现实中的不亦不趋,不拘于物象本身发展,总能突破束缚,将普通物象写出震撼人心的效果;创作思维是多维的,“地上”勿施,“空中”尽然,遨游天空,与月相邀,与风相披,大开大合,如仙人飞举、鲲鹏展翅,摆脱了尘浊俗情的牵绊,甚少常人的悲欢离合,面对挫折而速速开解,以豁达爽朗心态释然。在梦境、仙境、壮景、动景中,选用意象偏好江雨连山、烟波惊山等一类意象,隐隐呈现出“盛唐”气象的格调和追求。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李桂玉(女,笔名:六月桂花,成都大学汉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成都市金牛区聿童文学创作工作室创办人、校长)
配图 :方志四川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