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抒咏开天地 唯破常规才出奇——看歌剧《红船》如何展现党的一大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如何在歌剧舞台上对之做艺术化呈现?按照歌剧艺术的一般规律,历来讲究丰富曲折的情节、强烈的戏剧行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讲究“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以着力于人物的个性化塑造;而10多位代表参加的一大又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会前复杂的时代风云,“南陈北李”为建党所做的理论与组织准备,会间代表们的政论性发言和争论,会后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等,涉及人物众多,还不是单一的环境。其背景的宏阔和内容的丰富,远非长于抒情、拙于论理的歌剧及其有限时空所能承载。
浙江演艺集团推出的歌剧《红船》给出了如何用歌剧去演绎这样有难度的题材的答案。剧作家王勇打破常规、剑出偏锋,其剧本以非常之思建构了一个类似音乐中“回旋变奏曲式”的新型戏剧结构形态——以现在进行时的一大会议为主线,根据其地点的变更和议程的展开而予以变奏处理;以一大之前中国社会种种膏肓之疾、亡国灭种危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之苦,我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革命活动和建党筹划,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与婚姻等事情发生的广阔时代背景等过去时为插曲,通过贯穿全剧始终的时空交错的“意识流”手法,将会内会外、会上会下的众多真实与虚构人物、重大事件以及若干富有戏剧意味的场景编织进一个现在时与过去时频繁“闪回”、交替呈现的叙事框架中,使之有机连接、彼此作用。这种在广阔时代背景中取精用宏的佳思巧构,虽与歌剧常规结构和叙事逻辑相悖,但它确实是最适合全景式表现史诗性的宏大内容的创新型结构,同时也确立了《红船》一剧在“内容决定形式”原则下的叙事美学。
鉴于“南陈北李”及一大代表尽是男性,剧作家又将现在进行时的李达妻子王会悟和南湖船娘,以及过去时的杨开慧和湘籍逃难少女细妹子这4个女性角色有机融入剧情。此举满足了歌剧人物多样性和声部色彩丰富性的表现要求,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及舞台整体史诗性叙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对比元素。
孟卫东为《红船》作曲,使命崇高,任务艰巨,难题甚多。最大的难题,其一是如何达成恢宏而又碎片化的历史场景的音乐描写及其自然转接,其二是如何完成众多性格各异人物的个性化塑造,其三是如何将一大代表们某些政论性强于抒情性的剧诗化为具有歌唱美质的唱段。孟卫东从《国际歌》中选择其首句“起来”四度上行的号角音调为主导动机,以“这是最后的斗争”开始之三度级进下行音型为辅,运用移位、转调、扩张等手法贯穿在乐队或声乐声部中,使之成为统一全剧音乐的红色音响符号和主要结构力,并随剧情展开,在某些重要场面和时刻(如序幕合唱、陈独秀从陈望道手中接过《共产党宣言》译稿,直至尾声群众合唱《一个幽灵》的乐队前奏)不断鸣响,以期在观众听觉审美中形成气势磅礴、印象深刻的音响记忆。
在全剧音乐铺陈中,孟卫东着力营造了多个优秀的令人过耳难忘的音乐戏剧场面——由毛泽东首唱的《我有一个梦》,意蕴深邃而又诗意盎然,格调浪漫而又潇洒别致,后在剧中多次再现,具有主题歌的点睛功能;李大钊驾骡车送陈独秀出城一场,在乐队模仿骡蹄“得得”声的轻盈节奏衬托下,两位伟人的对唱与重唱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英雄气概纵论天下大势、共商建党伟业,音乐妙趣横生,画面生动;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对唱与二重唱,旋律悦耳,情真意切;一大代表在画舫上打麻将与吟诗相互交织时的男声对唱与合唱,谐谑而略带怪异,颇具喜剧意味。
本剧总导演黄定山在长期军旅生涯中养成了军人的浩然气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军旅艺术美学追求。他将《红船》体裁风格确定为“恢宏激荡、豪迈张扬、浪漫诗意、宏大叙事的史诗性歌剧”。在这一整体美学观的统摄之下,根据一度创作所设定的戏剧情境,以红船由部分到全景的展现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意象,通过推拉幕的灵活组合、复杂变化以及现代声光和影像技术的有效配合,非但奇迹般地完成了散碎戏剧场景的无缝连接,令情节的跳出跳进和时空的频繁转换如行云流水,颇具现代性美质;更为重要的,是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杨开慧、王会悟等人的情感抒发和形象刻画营造出一个又一个富有历史质感或诗情画意的时空情境。
同时,李大钊扮演者杨小勇、毛泽东扮演者王传亮、陈独秀扮演者严圣民、杨开慧扮演者郑培钦、王会悟扮演者唐琳等演员、交响乐队、合唱队、舞美操作团队,都在黄定山统一调度与指挥家王燕的协调配合之下,出色完成了所承担的任务,使得《红船》在各方面体现出较高水平。
当然,其中仍有一些艺术瑕疵有待改进。例如剧诗创作应该尽量减少政论性、加强诗意化的文学表达,宣叙调写作中应努力避免同音反复手法的过多运用,应加强乐队音乐在场景频繁切换时的连接功能以消除舞台节奏的停顿感等。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1日 1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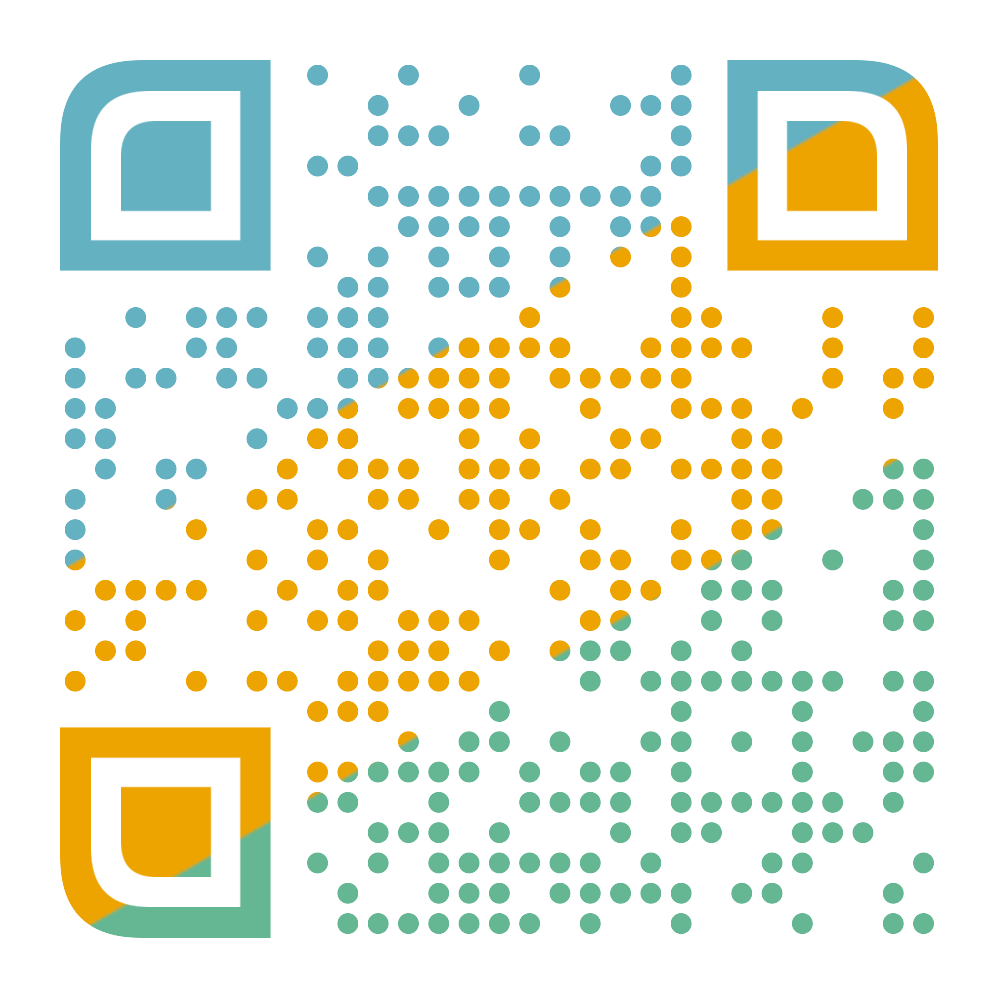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