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花盛开在现实的土壤中”——读长篇小说《止痛药》
陈仓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这也让他的小说带给人某种天然的信任:故事的真实和情感的真挚。《止痛药》(《中国作家》杂志2020年第1期)说的是一个以陕南农民身份进入上海的青年,却与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刻的联系,从此无法离开。小说以章节交替的形式,让发生在上海和陕西丹凤大庙村两个地方的故事交错呈现。
小说里的陈小元闯入上海并非偶然,他不是因为谋生打工才来到这里。上海是陈小元在乡村土炕上就梦想过的地方,他因为上海才出门,才打工谋生。陈小元一睁眼就与这座城市的代表性人物相遇,他被一个事后才知道叫凤姐的人一脚踢醒。而这位凤姐,是地道的上海人,本地大学毕业,外貌、气质、身份,有优越感。陈小元在懵懂的交流中,无意掉入了命运的漩涡,从此无力自拔。
陈小元这个在大庙村打棺材最多的木匠,与凤姐之间的差距无须分析。但陈小元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不怕别人嘲笑而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他因为差距太大而索性心底无私、坦坦荡荡。在上海与大庙村之间,陈仓搭建了一个极不稳定的平台,设置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关系。我想起陈仓的丹凤同乡——他的文学前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小说中的引生深爱着“村花”白雪,然而这是一种对方不但没有响应,甚至浑然无知的单向苦恋。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纯粹的爱情不可能是止痛药,反而是撒在伤口上的盐。白雪嫁给了在省城里有公职身份的同乡夏风。即使后者并无激情,但匹配度决定了稳定性。
《止痛药》里的人物关系其实走得更远。陈小元和凤姐完全不在同一个天空下。然而怕的就是一个人有了梦想而不顾一切去追逐,陈小元就是如此。梦想是一种意念,它不切实际却又异常执着,所以它也就不可能与时代同步变化,有时会显出概念化、“陈旧性”的特点。比如在陈小元和凤姐之间,导致他们不能在一起的阻力,不是白天鹅鄙视穷小子,倒是凤姐的母亲——一个典型的上海老太太横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永远无法走在一起。
凤姐的母亲显然是个概念化的人物,她只起一个作用,就是把凤姐推向一个“瑞士人”的火坑中,再把陈小元从凤姐的身边棒喝打走。这就注定了凤姐不可避免的悲剧,她不可能与那个“瑞士人”结婚,也不可能和陈小元走到一起。凤姐虽然看上去是个光鲜漂亮的知性女子,事实上却是完全受母亲管制的不幸女性。这样的人物设置,如此直白的表达,因此造成的悲喜剧,在今天至少不那么典型了。很多因素发生了改变,观念也有了变化,一些难以言说的理念,可能内化在骨子里,外在行为上可能未必会大打出手。但这就是陈仓单纯可爱的地方,他依据的是从前的想象,表达的是早已萌生的梦想,他对这种梦想必然要破碎早有自己的认定,于是他就在描绘这美好梦想的同时,又极力地用自己的笔拆毁它。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某种平衡。
这种平衡更集中地体现在陈小元的命运结局上,一方面他居然像中世纪的爱情追逐者一样,经历了仓皇跳窗而逃、导致终身残疾的惨剧;另一方面,他又似真似假地成了凤姐女儿的父亲。他就带着这种巨大的创伤和意外的“成果”重返大庙村。小说展开了一个极不平衡的双重世界。从中,我们读到了凤姐对陈小元缺乏依据却也因此更显纯粹的爱情,陈小元即使终身残疾也无怨无悔的执着,包括他对上海毫无怨言的眷恋。女儿凤妹不仅让他享受了亲情之爱,而且也让他和上海有了不可剥离的关系。他在痛苦中满足着。
读陈仓小说,有时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也让人想到郁达夫、庐隐等人小说里塑造的“烦闷”的“零余者”形象,特别单纯,异常执着。但陈仓不陷于哀怨、愤懑之中,有一种精神上的超脱和乐观。在《止痛药》里,他始终把陈小元塑造成一个乐观面对痛苦,朝着梦想跋涉的有志青年。陈小元为自己获得的每一点进步而兴奋,不因为屡受挫折而迁怒于任何人。他相信爱的力量,相信人生痛苦可以通过爱而缓解甚至治愈。他仍然坚信,爱是最好的“止痛药”。这爱,既有陈小元对凤姐,或陈小元与凤姐之间的爱情,也有陈小元对女儿凤妹无私的亲情之爱,以及女儿对他直到生命终点的付出与关爱。这是多么善良的愿望,而且“这理想之花就盛开在现实的土壤中”。
我曾经认为,贾平凹《秦腔》里败落的爱情,因为引生彻底的善良而得到弥补,这种以善作为爱情失败的补偿,也是很多中国小说家自觉不自觉的选择。在陈仓这里,我仍然读出了这一点,尽管陈仓为自己笔下人物开出的治愈痛苦的药方依然是爱。那是因为,他笔下那些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人物所理解的爱,从一开始就包含极其深厚的善的元素,爱与善本来就是融为一体,从未分开的。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1日 16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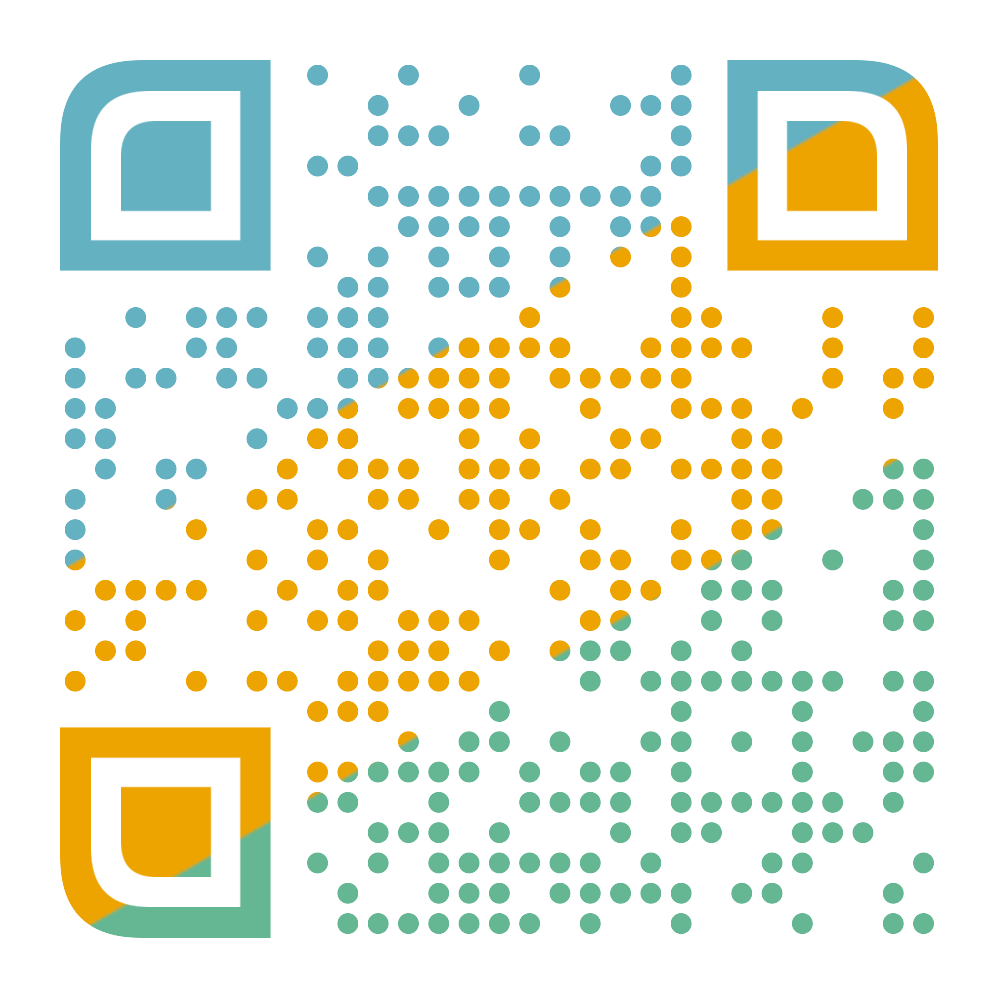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