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花寻鸟在米易
作者:龙仁青《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1日 14版)
【生态文学】
2019年年底,去了一趟四川米易,也是我第一次去米易。
在米易,朋友告诉我,从他们这里,去自己的省会城市成都要走近600公里路,而去邻省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却只有300多公里,少了大概一半的路程。所以他们经常要去昆明“浪浪”,“比成都还熟悉”。米易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他们在选择上有了偏重。我也在网上百度过米易的地理位置,让我感兴趣的,是它和我的故乡青藏的关系: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雅砻江与安宁河交汇处。于是我便想,也许是从我的家乡一路走来的雅砻江在这里遇见了安宁河,他们就像是沿着江畔河岸相向而行的一对陌路男女,在擦肩而过的瞬间相视而笑,并在江畔河岸的拐弯处停下来休息,彼此寒暄几句,便迸溅出了爱情的火花,他们把彼此交付于对方,灵肉相融,于是便孕育出了米易——在米易的血脉里,有着青藏的染色体,比如这里的蓝天,空广通透,这里的阳光,明媚率真,完全是青藏的遗传。
米易的夏天,长达几近半年,即便是夏天过去,这里的草木依然葳蕤。我们到达的时候,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此刻是他们的冬天。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的故乡青藏,冬季冗长又寒冷,我出发的时候,南部的玉树、果洛正在落雪。听了朋友的话,看着满眼的碧绿以及碧绿所簇拥着的姹紫嫣红——这明明是故乡初夏时节的模样——心里微微生出一丝不好意思来,有点儿嫌母丑的自卑。我的故乡,夏天是那么的金贵,高海拔地区,夏天逗留的时间也就一个多月,逼迫那些花草们珍稀着夏天的每一寸时光,加紧完成着它们从开花到结果的生命历程,而米易的花花草草们却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它们有的是时间,把夏天大把大把地挥霍。
去米易的时候,专门带上了相机。那几天里,我带着相机散漫地行走,被我框入画面的,便是米易随处可见的各种花鸟。
阳光是米易的朋友极力推荐的,说他们的宣传用语便是阳光米易,“冬天到米易晒太阳”——或许就是父亲一样的雅砻江赋予了米易高原一样敞亮的性格,米易的天气似乎从来没有过心情不好的时候。在米易的几天里,阳光毫不吝啬地普照着大地,让米易的每一天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晴朗。
阳光是花卉的同谋,它们分解阳光的颜色,再用这些颜色标榜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让我们的肉眼能够轻易地看到太阳纷繁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其实,到米易的第一天,走出机场,坐在去往县城的大巴上,就看到了马路两旁招摇的色彩,那是三角梅,一丛丛一簇簇地开放着,自在随意地抛头露面,就像是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的讨生活的打工者,身上随意地穿着牛仔裤T恤衫,行色匆匆,没有半点儿娇贵的意思。在我的家乡青藏,三角梅也是有的,但它们都是种植在花盆里,养花人每天悉心伺候着,怕冻着,怕热着,怕干着,怕淋着。白天端到阳台上晒太阳,晚上降温了赶紧端进内屋里。如此,它们便像是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小家碧玉,足不出户,小姐脾气。
在我的家乡,三角梅只是承担了观赏植物的角色,而在米易,在广大的南方中国,三角梅更多地承担着城市绿化植物的身份,是不同的地域和物候,赋予了它不同的性格和气质。三角梅是明显的被子植物,被子植物作为开花植物的祖先,三角梅依然保留着它们先祖初始的样子——三角梅,又名三叶梅,它们的花瓣——其实是花苞,真正的花朵不起眼地掩藏在花苞内——依然有着叶子的形状,只是在颜色上与自己的叶子区别开来,占领着叶子中最顶端抑或最显著的位置。如此,这个在南方极为普通的花卉,却可以把历史上溯到动物和植物分家的寒武纪时代。当动物和植物各自选择了四处游走和岿然不动,放下了一切的植物却唯独放不下爱情,于是,它们以公开贿赂的方式,吸引那些会飞的传粉动物为自己做媒婆,把它们的浓情蜜意带给心仪的情人。它们拿给传粉者的,有艳丽的色彩,有扑鼻的芬芳,更有让传粉者一经沾染从此便不能自拔的花蜜。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它们把希冀交给漫长的进化,在日积月累的时间的尘埃里,它们一代代地死去又一代代地复活,渐渐地,它们的几片叶子慢慢有了花的形状。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花瓣——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它不是花苞,那不同层次不同深浅的红,虽然在颜色上背离了叶子,但它依然保留着叶子的样子,执着地存储着自己先祖的形象,每一抹红里都满含着对远古的追思和怀念。
花卉引诱传粉动物让它们的爱情开花结果。这是世间的花儿一开始就与传粉动物达成的协议,亿万年来,它们严格履行协议,恪守当初的约定。迄今,那些鸟儿,那些昆虫,还有其他的传粉动物,从来没有违背过它们与花儿的契约。
到了米易,我们入住的酒店在县城郊区,虽然张扬出了现代城市的工业化气息,但野蛮生长的绿植却也不甘示弱地围拢在酒店周围。不动声色中,人类建筑与自然田野在这里摆开了阵势,似是要来一场博弈,一比高低。走出酒店大厅,向右,便是一座花园,大片的草坪,有溪流劈开草坪蜿蜒流过,周边有高大敦实的棕榈树、椰子树,掺杂其间最茂盛的,依然是三角梅。来到米易的翌日清晨,啁啾的鸟鸣叫醒了我,我在鸟鸣的指引下走进了花园。很快,就在三角梅的枝叶间见到了小巧的鸟儿。这鹅黄浅绿间杂的可爱小鸟叫灰腹绣眼鸟,这是一种栖息于海拔1200米以下地区的鸟,在我的家乡踪影难觅。
忽然想起曾在网上见过的宋徽宗赵佶的绢本画:形如盘虬的梅枝从画面左侧伸入,枝上是几朵稀疏的梅花,孤零清浅。在一枝极力向上的梅枝上,立着一只小鸟儿,嘴喙微启,正在孤独地鸣唱。或许,它正在召唤着自己的情侣,从那疏朗的天空飞入画面,与它一起共享这深宫里的春天。这幅作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名为《梅花绣眼图》,有专家认为枝上的鸟儿便是灰腹绣眼鸟。我不通书画,对古画更是知之甚少,就自己有限的浏览,似乎极少见到绣眼鸟入画者,所以只一眼,便永远记住了这幅画。
三角梅与绣眼鸟,似乎是花卉与传粉者之间的关系,三角梅因此为绣眼鸟提供了觅食与藏身的空间——绣眼鸟总是在枝叶间快速地飞舞跳跃着,相机很难捕捉到它的身影。而绣眼鸟的飞舞跳跃,也为掩映在三角梅深处的雄蕊和雌蕊,提供了谈情说爱、生儿养女的可能。后来从资料里得知,由于三角梅花蕊的雌蕊深藏在几个雄蕊的底部,很难达到传粉的目的。于是我想,这也许是植物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完美吧,一种至今还保留着起源形态的花儿,或许是一种怀旧而又稍显笨拙的花儿,它经常沉浸在纷繁往事之中不能自拔,错过了几多机遇,让自己进化的步伐远远地滞后于其他的花卉。如此,它还没有学会对传粉者过多的阿谀讨好,也让自己的花卉和花苞保持着从叶子成为花卉的过渡状态。
说起花卉与传粉者的关系,忽然就想起那一束龙牙花。那天清晨,我一进入花园,便看到一只蜜蜂来得比我还早,它嗡嗡地飞着,围绕着一只伸向天空的龙牙花悬停或者快速地迂回,似是躲避着什么,又不愿舍弃眼前的诱惑。我举起相机,把龙牙花和那只蜜蜂框进了同一幅画面。我不知道龙牙花御用的传粉者是谁,但就我的经验判断,龙牙花庞大的花束显然不是娇小羸弱的蜜蜂可以对付的。看到那小小的蜜蜂执着地围绕着硕大的龙牙花飞舞,忽然就想起“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句诗,也对这只早起采蜜的小蜜蜂产生几分怜悯之情,与怜悯间杂的,是更多的敬佩。不论人或者动物,知难而进都是值得尊重的品质。
在花园里看到北红尾鸲,让我有些惊讶又兴奋不已。北红尾鸲的名字,之所以在字首冠以“北”字,是因为它繁殖生息在北方,是北方常见的鸣禽。在我的家乡民间,北红尾鸲被叫作“火焰燕”,“火焰”是指它腹部如火燃烧的颜色,而“燕”则纯属民间鸟类科属划分,猜测是因为北红尾鸲落在地上时,有不时翘尾的习惯,形同燕子,故名。在米易看到北红尾鸲,雅砻江滔滔不尽的波涛声顷刻间便在我的耳畔回响开来。正是这条河流,打通了鸟类迁徙的通道,让北红尾鸲以河流为方向,来到温暖的米易过冬。河流所打开的,不仅仅是动物迁徙的通道,人类的文明,也是沿着河流,或上溯、或下延,在河流的岸畔碰撞融合,逐渐壮大。不同的文明,只要有河流牵线,在每一种文明里都能看到其他文明的火花闪现,看到它们结缘,牵手,俨然一体。
或许,这也是我在米易,时时有一种熟悉而亲近的味道萦绕心头的缘由。
(作者:龙仁青,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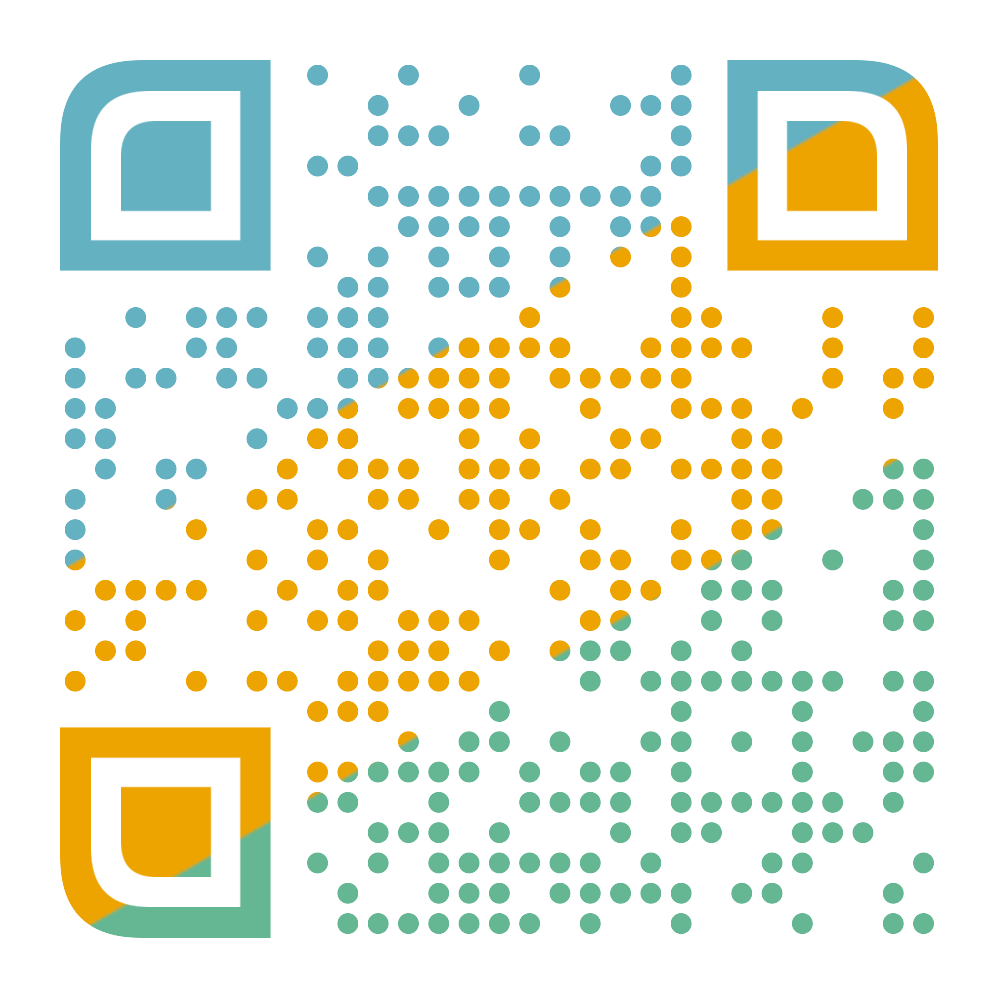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